#阿酸不妙屋
Explore tagged Tumblr posts
Text
Getting into college is like being pregnant. Everyone congratulates you, but they never think about how many times you've been fucked to death
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如是舍利子!法身所顯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乃至一切眾生,若男若女童男童女,有貪恚癡熱惱病者,至菩薩所暫觸其身,一切病苦皆得消滅,又覺其身離諸熱惱。何以故?由諸菩薩摩訶薩本發大願善清淨故。
——摘自《大寶積經 (第48卷)》
又舍利子!證得法身菩薩摩訶薩,亦以大願自嚴持身為法良藥,善能息滅無量眾生三毒熱惱,乃至息滅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眾生貪瞋癡等諸惱熱病。
「復次舍利子!如我先說,證得成就法身菩薩摩訶薩願力持身而為良藥,用滅無量不可說眾生煩惱熱病。如是等相,吾今更說,汝當諦聽。舍利子!我念往昔過無數劫有佛興世,名曰然燈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舍利子!爾時然燈如來、應、正等覺為我授記,作如是言:『汝摩納婆!於當來世過阿僧企耶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乃至佛、薄伽梵。』舍利子!彼然燈佛授我記已,爾時便證法身成就。佛滅度後,我為帝釋名微妙眼,於三十三天,得大自在、具大神通、有大威德、宗族熾盛。舍利子!是時贍部洲中有八萬四千大城,有無量千村邑聚落市肆居止,復有無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一切眾生住如是處,人物繁擁極為興盛。舍利子!當於爾時有大疫病中劫出現,多有眾生遭遇重病,身體潰爛、癰腫痤癤、疥癬惡瘡、風熱痰癊,互相違返。以要言之,一切病苦無不畢集。於時復有無量百千諸醫藥師,���欲救療如是病苦,勤加功用極致疲倦,而眾生病無有愈者。舍利子!彼諸無量病苦眾生不遇良醫,為病所弊,無有救護、無有歸趣,皆共呼嗟,失聲號哭涕泣橫流,作如是言:『我今受此無量重病。何處當有天、龍、藥叉、健達縛及諸羅剎、人非人等,以大慈悲而能見為除我病者?若有能除我病苦者,我當不悋一切財寶厚報其恩,隨其教誨。』舍利子!我於爾時以淨天眼超過於人,見諸眾生種種疫病逼惱其身,煩冤纏繞無有救濟。又以天耳清淨過人,徹聽眾生號訴之聲,極為悲怨酸楚難聞。舍利子!我於彼時見聞是已,於是眾生深起大悲,即作是念:『一何苦哉!如是無量無邊眾生遭是重病,無舍無宅、無救無護、無歸依趣、無能療者。我今決定為諸眾生為舍為宅、為救為護、為歸依處、為醫療者,必令病惱普皆平復。』舍利子!我於爾時便隱帝釋高廣之形,於贍部洲俱盧大城不遠受化生大眾生身,名曰蘇摩。既受生已,住虛空中,以伽他頌遍告贍部洲內所有眾生說其頌曰:
「『俱盧大城為不遠, 有大身者名蘇摩,
若有眾生噉其肉, 一切病惱皆除愈。
彼無瞋恚諸忿害, 為作良藥生贍部,
汝當欣踊勿驚疑, 隨意割肉除眾惱。』
「舍利子!爾時贍部洲內所有諸城八萬四千村落市肆,又無量千一切含識為病惱者,聞是聲已,一時皆往俱盧大城蘇摩菩薩大身之所,競以利刀或割或截彼之身肉。舍利子!蘇摩菩薩行精進行,當被割時於其身內出大音聲,說伽他曰:
「『若此能實證菩提, 智藏當成無盡者,
隨我所發諦誠言, 亦願身肉常無盡。』
「舍利子!爾時贍部洲內一切眾生為病逼故,段段割截菩薩之身,或擔持去、或就食者。雖被加害,以願力故隨割隨生無有缺減。舍利子!是諸眾生噉食蘇摩菩薩肉已,一切病患悉皆除滅。病既除差,復令眾生心得安樂形無變易。是諸眾生身心安樂,展轉聲告遍贍部洲。來食肉已,病皆除愈無有變易身心安樂。舍利子!爾時一切贍部洲中人民之類,若男若女童男童女,食菩薩肉病除愈者,於是菩薩深懷恩慧競自思惟:『是蘇摩者極有重恩,除我病苦施我安樂令無變易。我當云何施設供養酬斯厚澤?』作是念已,咸共集會詣俱盧大城蘇摩菩薩大身之所。既到彼已皆共圍繞,感戴其恩不能自勝,說伽他曰:
「『仁為舍宅為救護, 仁為良醫妙藥者,
唯願哀憐垂教勅, 我等��何修供養?』
「舍利子!我於爾時為是大身,拔濟眾生如是病苦,知是無量諸眾生等銜我重恩歸依我已,便滅所現蘇摩大身,復帝釋形住眾生前,威光顯盛而告之曰:『卿等當知,若為病苦由我身肉而得除差,卿等懷恩將思報者,卿等當知,我本不為村城館邑王都國土田宅舍屋住處等事愍卿病苦行身肉施,我亦不為金銀末尼琉璃真珠珂貝璧玉珊瑚等寶行身肉施,我亦不為象馬牛羊放牧畜產行身肉施,我亦不為婦人丈夫童男童女奴婢僕使行身肉施,我亦不為餚膳飲食衣服臥具病緣醫藥及餘資蓄行身肉施,我亦不為園林池苑宮殿樓觀愍卿病苦行身肉施。卿等當知,我本所以愍卿病苦行身肉施,為令眾生離不善業。卿等但能為我永斷永離殺生之業、永斷永離不與取業、永斷永離欲邪行業,如是永斷永離虛誑語業、離間語業、麁惡語業、綺飾語業、貪欲瞋恚諸邪見業。卿等於此永斷離者,是為利益,是為報恩。』舍利子!爾時帝釋復為大眾說伽他曰:
「『我非為求珍寶聚, 其量高廣等迷盧,
亦不為求天玉女, 及諸衣食床敷事。
欲奉蘇摩大身者, 但當尊重同和合,
展轉慈心相敬視, 專修淨妙十業道。
卿等當於十業道, 但常和合堅防守,
是名大興法供養, 菩薩非求世財故。
我不用諸世財寶, 芳羞飲食妙衣服,
象馬車乘牛羊等, 床敷婇女資生具。
卿等但共同和合, 善持清淨十業道,
展轉發起大慈心, 彼此熏修利義意。』
「舍利子!爾時贍部洲內無量眾人聞我說是勸發之言,感恩德故頂禮我足,皆悉受持十種清淨妙善業道。舍利子!我於爾時為彼大眾廣宣正法示教讚喜,便隱天身不現於世。如是舍利子!我正憶念往昔世時贍部洲中,所有人民食噉蘇摩菩薩肉者,從是已來,乃至無有一人墮於惡趣。彼命終已,皆生三十三天,宿業力故與戒俱生。舍利子!我於爾時復為彼天隨其所應敷演法化示教讚喜,皆令安住聲聞乘中、或獨覺乘、或有安住阿耨多羅一切智乘。如是等眾聞我法故,或有已般涅槃、正般涅槃、當涅槃者。舍利子!汝觀如是安住法身菩薩摩訶薩行毘利耶波羅蜜多故,成就如是大神通力,成就如是大威德力,成就如是大勢之力,乃能但捨一身之慧,而大成熟無邊眾生皆住三乘得不退轉。」
——摘自《大寶積經 (第48卷)》
https://deerpark.app/reader/T0310/48#0282b26.11)




5 notes
·
View notes
Text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MINATOMO NO YORITOMO
アイウエオカキクケコガギグゲゴサシスセソザジズゼゾタチツテトダ ヂ ヅ デ ドナニヌネノハヒフヘホバ ビ ブ ベ ボパ ピ プ ペ ポマミムメモヤユヨrラリルレロワヰヱヲ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みむめもやゆよらりるれろわゐゑを日一国会人年大十二本中長出三同時政事自行社見月分議後前民生連五発間対上部東者党地合市業内相方四定今回新場金員九入選立開手米力学問高代明実円関決子動京全目表戦経通外最言氏現理調体化田当八六約主題下首意法不来作性的要用制治度務強気小七成期公持野協取都和統以機平総加山思家話世受区領多県続進正安設保改数記院女初北午指権心界支第産結百派点教報済書府活原先共得解名交資予川向際査勝面委告軍文反元重近千考判認画海参売利組知案道信策集在件団別物側任引使求所次水半品昨論計死官増係感特情投示変打男基私各始島直両朝革価式確村提運終挙果西勢減台広容必応演電歳住争談能無再位置企真流格有疑口過局少放税検藤町常校料沢裁状工建語球営空職証土与急止送援供可役構木割聞身費付施切由説転食比難防補車優夫研収断井何南石足違消境神番規術護展態導鮮備宅害配副算視条幹独警宮究育席輸訪楽起万着乗店述残想線率病農州武声質念待試族象銀域助労例衛然���張映限親額監環験追審商葉義伝働形景落欧担好退準賞訴辺造英被株頭技低毎医復仕去姿味負閣韓渡失移差衆個門写評課末守若脳極種美岡影命含福蔵量望松非撃佐核観察整段横融型白深字答夜製票況音申様財港識注呼渉達良響阪帰針専推谷古候史天階程満敗管値歌買突兵接請器士光討路悪科攻崎督授催細効図週積丸他及湾録処省旧室憲太橋歩離岸客風紙激否周師摘材登系批郎母易健黒火戸速存花春飛殺央券赤号単盟座青破編捜竹除完降超責並療従右修捕隊危採織森競拡故館振給屋介読弁根色友苦就迎走販園具左異歴辞将秋因献厳馬愛幅休維富浜父遺彼般未塁貿講邦舞林装諸夏素亡劇河遣航抗冷模雄適婦鉄寄益込顔緊類児余禁印逆王返標換久短油妻暴輪占宣背昭廃植熱宿薬伊江清習険頼僚覚吉盛船倍均億途圧芸許皇臨踏駅署抜壊債便伸留罪停興爆陸玉源儀波創障継筋狙帯延羽努固闘精則葬乱避普散司康測豊洋静善逮婚厚喜齢囲卒迫略承浮惑崩順紀聴脱旅絶級幸岩練押軽倒了庁博城患締等救執層版老令角絡損房募曲撤裏払削密庭徒措仏績築貨志混載昇池陣我勤為血遅抑幕居染温雑招奈季困星傷永択秀著徴誌庫弾償刊像功拠香欠更秘拒刑坂刻底賛塚致抱繰服犯尾描布恐寺鈴盤息宇項喪伴遠養懸戻街巨震願絵希越契掲躍棄欲痛触邸依籍汚縮還枚属笑互複慮郵束仲栄札枠似夕恵板列露沖探逃借緩節需骨射傾届曜遊迷夢巻購揮君燃充雨閉緒跡包駐貢鹿弱却端賃折紹獲郡併草徹飲貴埼衝焦奪雇災浦暮替析預焼簡譲称肉納樹挑章臓律誘紛貸至宗促慎控贈智握照宙酒俊銭薄堂渋群銃悲秒操携奥診詰託晴撮誕侵括掛謝双���刺到駆寝透津壁稲仮暗裂敏鳥純是飯排裕堅訳盗芝綱吸典賀扱顧弘看訟戒祉誉歓勉奏勧騒翌陽閥甲快縄片郷敬揺免既薦隣悩華泉御範隠冬徳皮哲漁杉里釈己荒貯硬妥威豪熊歯滞微隆埋症暫忠倉昼茶彦肝柱喚沿妙唱祭袋阿索誠忘襲雪筆吹訓懇浴俳童宝柄驚麻封胸娘砂李塩浩誤剤瀬趣陥斎貫仙慰賢序弟旬腕兼聖旨即洗柳舎偽較覇兆床畑慣詳毛緑尊抵脅祝礼窓柔茂犠旗距雅飾網竜詩昔繁殿濃翼牛茨潟敵魅嫌魚斉液貧敷擁衣肩圏零酸兄罰怒滅泳礎腐祖幼脚菱荷潮梅泊尽杯僕桜滑孤黄煕炎賠句寿鋼頑甘臣鎖彩摩浅励掃雲掘縦輝蓄軸巡疲稼瞬捨皆砲軟噴沈誇祥牲秩帝宏唆鳴阻泰賄撲凍堀腹菊絞乳煙縁唯膨矢耐恋塾漏紅慶猛芳懲郊剣腰炭踊幌彰棋丁冊恒眠揚冒之勇曽械倫陳憶怖犬菜耳潜珍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190K notes
·
View notes
Text
至誠懇切,預約幸福
以下同一位有緣人分享:
分享一
家母近來坐著的時間越來越���,經常看半小時電視後,就請外勞推她進房間休息。說是休息,但全身酸、麻、痛,加上肛裂,真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近醫生開了癌末病人用的類嗎啡藥物,讓她稍稍可以安眠、減緩疼痛,但剛開始藥量太強,經常眩暈不適,難以兩全。
母親節時,大家坐在客廳慶祝,家母淡淡的說已經7年多了,手不能拿、腳不能站,身上的疼痛有增無減。我看著她,眼睛不覺濕潤起來,是多大的罪過,要忍受這無盡的地獄煎熬;是多麼的堅忍,才能熬過這看不到盡頭的苦難。
親愛的母親,我們知道您堅強的外表,是不願讓子女擔心的母愛,苦苦的忍耐,是不忍就此離去,留下哀傷的子女。我無法代您受這千辛萬苦,這箇中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能夠確信的是,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苦盡必有甘來,淬鍊之後必成真金。
《達磨大師血脈論述記》:「本心就在自己的見、聞、嗅、嚐、覺、知當中,時時現前,只因為眾生起心攀緣外境,執境為實,而不見本心。」、「所以夢未醒時,念念著相,被夢境所困,不知全夢即心,及至夢醒之時,猶如破相顯性,當下即見全夢即心,夢境中的五藴、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無一不是心體,心外無別夢。」
我們在這娑婆世界中,以為只有眼看到的、耳聽聞的、鼻嗅到的、口嚐過的、手摸到的才是真的,要能在苦難中覺知所受是夢、是幻、是泡、是影,何其難哉!但家母說:「我痛苦時,就求觀世音菩薩,就唸阿彌陀佛。」能夠知道唸佛又何其有福。就是這樣一念至誠,一心佛號,夢醒時分,得大自在。
分享二
沒想到後來,母親承蒙佛菩薩慈悲開示:「《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各900部,可預先超拔,往生後,可直接到中天報到,享天福100年。」感恩阿伯,感覺天很黑,突然出現了一盞明燈,喜出望外。
(分享結束)
小編看到這篇分享文的時��,真的是眼淚直流。沒有走過病苦的人,可能真的難以想像,全身的酸、麻、痛、刺、癢,站也不得、坐也不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日復一日地,心靈被綑在全身疼痛的身體牢籠中,在無間地獄中苦苦煎熬。
但是為了家人只能撐住,不抱怨了,因為抱怨也沒用,就如有緣人的母親,只是淡淡地說著身體的苦痛與不適,沒有哭天搶地或激動情緒,因為再多的訴苦只是增添家人的煩惱。有緣人的母親早已明瞭,此時能救她的只有佛菩薩,她說:「我痛苦時,就求觀世音菩薩,就唸阿彌陀佛。」
有緣人曾經把母親的故事寫成分享文,以下摘錄自〈我好希望菩薩開示是「業障討報」!(三) 〉分享二:「105年10月,80歲的父親因整修房屋,自3公尺高處摔落,剛好壓到母親,父親沒有受傷,母親則頸椎第3、4節受傷,四肢癱瘓。是何因果呢?佛菩薩慈悲開示:『係因父母親2人,前世因利益衝突,共同犯下了拿刀殺業主菩薩導致傷重成之罪業,父親因為對母親有恩,所以由母親代為受報,2人各需唸誦經文各118遍迴向給業主菩薩。』
此筆業力回向圓滿後,母親轉至復健病房數月,106年3月又昏倒住進加護病房,開示出新業障:『係因前世利益衝突,用棍子打人家致傷重半身不遂,需誦經文各115遍』,緊急回向圓滿後,終於在3月底前出院返家休養。」(摘錄結束)
105年10月至今,已過了七年半,有緣人的母親就這樣在人間地獄中度過無數個夜晚。有緣人非常孝順,經常講因果觀念給母親聽,鼓勵母親念佛。只是,人的業力不可能只有一兩筆,這些年的病情起伏,有緣人仍幫母親持續消業障。也有能力請外勞,照顧母親的基本日常需求。
但是,平心而論,這世上苦難的人何其多,因意外、疾病造成癱瘓、半身不遂,多少的家庭因為親人殘疾而飽受磨難,這一切真的是意外嗎?不是,是因果相欠!用現世的苦體會冤親債主當年的痛。誠如上述分享摘錄,有緣人的母親也曾經造成業主菩薩傷重致死或半身不遂,讓業主菩薩及其家人承受人生的悲苦與磨難。
有緣人說:「如果能夠早點知道母親前世種下什麼因,在惡果還沒來臨之前,就先與業主菩薩達成和解,用自己能力所及的誦經方式,把該還的債還清,化解前世重大罪業,比起事後過著頭腦清楚但四肢不能動,卻又痛、癢、麻、痠,且夜晚不能成眠,如地獄般的日子,該有多好。」
遇到牟尼精舍以「因果債,功德還」因果化解後,雖然有緣人母親的身體已無法復原,但是她開始有了堅定的信仰,多年來在苦痛中堅毅地唸佛。終於蒙佛菩薩開示,可為其預先超拔。我們幫有緣人的母親送件請示佛菩薩,請示一:「三經九百部,是否已包含從地府到平民區,再到中天的經文?」開示:「全包括」。
請示二:「可以預先超拔,是因為1.母親受報時,心性有磨練到,所以苦盡甘來?2.母親受報時,子女代為誦經消業,自己也唸佛。3.子女在精舍的修行,對母親有幫助?有緣人本身從事公職工作,有累積功德福報,對母親有幫助?」
佛菩薩開示:「都有幫助,但最主要的是,在苦難中她悟徹人生,竭誠唸佛,數雖不多,其心剴切,唸佛聲感動佛菩薩,出手搭救。」所以,是人間受苦代替了地獄刑罰,同時在苦難中沒有放棄,反而不斷懺悔唸佛,終因至誠感動佛菩薩了。
有緣人和其母親都有接觸佛法的大福報,有緣人幫母親消業做功德,感得母親從鬼門關出來,從四肢癱瘓不能言語,到可以返家休養,還能開口唸佛。《地藏經》:「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臨命終時,神識惛昧,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是諸眷屬,當須設大供養,轉讀尊經,念佛菩薩名號。如是善緣,能令亡者離諸惡道,諸魔鬼神悉皆退散。」
但是,真正能讓有緣人的母親脫離四肢癱瘓苦難的,還是母親她自己對佛菩薩至誠懇切的憶念與交託。《地藏經》:「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天若人,隨業報應落在惡趣,臨墮惡趣中,或至門首,是諸眾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句一偈大乘經典,是諸眾生,汝以神力方便救拔,於是人所,現無邊身,為碎地獄,遣令生天。受勝妙樂。」有機緣能幫助母親往生天上,是她自己至誠懇切。此事要天也要人,自助、人助、天助,而得佛菩薩出手相助。相信以有緣人的孝順,定能盡快為母親超拔離苦。
《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清楚地指出將「色、受、想、行、識」五蘊都拋開,心態不被自己的主觀意念所左右,才能解救一切的痛苦跟災難。恭喜有緣人的母親,看破人世迷霧,讓佛菩薩牽著手,走到離苦得樂的彼岸。風雨即將結束,下一站預約幸福。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韋馱菩薩
南無伽藍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




0 notes
Text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梦——评《春光乍泄》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李白《月下独酌》
有人说,如若从��港的维多利亚港潜入海底,穿越地心,便到达了对香港而言的世界尽头——布宜诺斯艾利斯。而王家卫把故事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理由是:要让演员体会到一种绝望,并把绝望带进电影中。因为这“最远”的距离与绝望,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不会是意外。
《春光乍泄》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一对不被世俗认可的恋人,黎耀辉和何宝荣,从香港逃离到阿根廷,本来应该是春光明媚的生活,却在电影的开头蒙上了黑白滤镜。在共同经历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彼此失去信任的二人作别,黎耀辉回到了香港的家中,何宝荣却永远定格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租屋内。
“春光乍泄”的片名,猛一看便带有些许的香艳意味,影片中王家卫导演十分大胆地拍摄了许多亲密镜头。而“光”的意象,在影片中有多处体现:不论是黎耀辉为何宝荣做饭时,窗外泻下的一缕微光;还是黎耀辉在露台上工作时明媚的阳光;亦或是二人在厨房里翩翩起舞时的温暖的白炽光,“光”总是带给观众温暖的感觉。二人相处的美妙时光总是浓墨重彩的,仿佛只因拥有彼此,这个世界才带有色彩;而当两人分离时,一切便重归黑白。
《春光乍泄》的英文片名是“Happy Together”,正因两人是在一起happy的,终有一日,当两人不再一同快乐地挥霍时光,而是趋于平淡地同甘共苦,这部电影便不复存在。英文片名限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黎耀辉与何宝荣注定不可能一辈子只追逐共同拥有的快乐,最后二人的分道扬镳也使得曾经共同快乐的时光显得弥足珍贵。
故事的开头是何宝荣在地摊上买了一盏旧台灯(台灯是整部电影暗藏的线索),台灯上描绘的是壮丽的伊瓜苏大瀑布,二人便驱车前往,但在途中迷路,在灰蒙蒙的色调中,二人争吵不断,最后何宝荣撂下一句“不如分开一下”便转身离开。影片开头中,黎耀辉十分无奈地说了一句“不如从头开始,这是何宝荣的口头禅”,在一幕中,黎耀辉捂脸时的无助与痛苦将内心的情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因为他的付出与迁就换来的只有何宝荣一次次没有理由的离开,这种痛苦又随着何宝荣不断回归与离开中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形成恶性循环。我想在这里,黎耀辉的耐心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本就是十分不易的,二人对香港的“逃离”后的甜蜜,似乎在一次次争吵与分离中消散殆尽。
何宝荣离开后,黎耀辉为了生计在酒吧打工,招揽生意,但是他遇到了和外国人在一起腻歪的何宝荣,本来嘴角带有一丝职业化微笑的黎耀辉周遭温度骤降,特别是在看到何宝荣与外国人激吻时,他只能站在门口。镜头转到何宝荣,他在车中点燃一支烟,脸上的狡黠好像预示着他料到黎耀辉一定会追上来,但是当过了几分钟他没有看到黎耀辉的踪迹时,他无力地瘫在座位上,脸上带着失望与落寞,进而转变为一种冷漠。在一分钟内完成“笃定自若与得意,再到局促不安、再到失望落寞,最终冷酷”的转变,张国荣的演技使我深深折服。
在与何宝荣重逢后,原本好脾气的黎耀辉却不再显得那么淡定,遇见吵闹的旅客也失去了为他们拍照的兴致,再次与何宝荣的见面,他只敢躲在酒吧里面,等何宝荣离开之后才敢出现。当何宝荣出现在黎耀辉家门口,两人扭打在一起,这个时候黎耀辉不再淡定,他的愤怒与嘶吼,不仅是对何宝荣放荡不羁的怨恨,更是对自己无法控制爱恨交加又嫉妒万分情感的懊恼。何宝荣的一句“我好想你陪我一下”却让黎耀辉夺门而逃,或许他害怕自己再次原谅何宝荣,开启另外一个恶性循环。
当何宝荣受伤后再度出现在黎耀辉家门口时,影片由黑白转为彩色。黎耀辉为他洗衣服、洗澡、做饭,两人似乎回到了快乐的时光。因为爱一个人,黎耀辉可以在感冒时为他炒饭、可以陪他去自己毫无兴趣的马场、可以爱上他的爱好——跳舞。两人共舞的这个片段是我在全片中最爱的场景。先前笨拙而认真学习跳舞的黎耀辉,镜头一转,在厨房中的二人翩翩起舞,温暖的黄色微光泻下,仿佛整个世界中只有彼此,二人笑意浓浓。这在一刻,什么舞步、音乐、节奏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拥有,随后的深情一吻,或许是由于先前的分离,两人似乎都打开了心扉,倘若时间能够停滞在这一刻该有多好。
猜忌和怀疑往往是摧毁爱情的利器,张宛的出现使得二人中出现嫌隙,这个用耳朵感受世界的男人,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玩笑,便摧毁了黎何二人本就如履薄冰的爱情。黎耀辉不知道何宝荣会因为自己不喜欢他在夜晚穿着光鲜而在家中等他,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争吵中的一句“我不是你”会给何宝荣带来多大的心理伤害,或许“我不是你”的下一句是“那么下贱”。而对何宝荣而言,与黎耀辉的争吵似乎是二人对感情的证明与发泄,明明已经伤痕累累却依旧要互相伤害,冷战磨去了他的耐心,终于在争夺护照中爆发,这时候的二人已经不信任彼此了,又一次扭打后,何宝荣离开了。
黎耀辉最终还是一个人前往伊瓜苏大瀑布,在瀑布的拍打中,他的脸上早已无法区分瀑布与泪水,而何宝荣也在黎耀辉的家中发现自己曾经买的台灯画的是两个人一起看瀑布的画面。黎耀辉在回香港前在台湾停留,此时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他在张宛家的店铺吃饭,最后拿了一张张宛的照片,张宛是他对的阿根廷之旅的纪念,而当他看到这张照片,就能想起那个他无法忘怀却也无法面对的身影。
如果说黎耀辉与何宝荣有什么共同点,我想是缺乏安全感与自卑。影片中,梁朝伟扮演的黎耀辉和我一直认知的梁朝伟并没有太多差别,他好像永远是沉默的,只有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才会露出情绪变化。在香港二人的爱情无法被接受,来到阿根廷好不容易和爱人团聚又害怕爱人不按常理地离去,当木讷的他偷偷藏起何宝荣的护照时,我想他的目的其实十分单纯,正是因为害怕失去,才会有一种想要把爱人拴在身旁的欲望。但是他忘记了一点,感情和流沙共通:越是想要握紧却流逝得越快。黎耀辉在香港有家,有父母,有工作,但是他为了和何宝荣在一起,选择离开家在外流浪。其实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家可回,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等他回家。
张国荣扮演的何宝荣是一个既自卑又自负的形象,当他与黎耀辉扭打时,他问黎耀辉是否后悔和自己在一起,其实这个时候的他内心是十分没有底气的,在他人面前一贯嚣张的他却在黎耀辉面前显得十分卑微,当他最后一次回到黎耀辉的家中打扫时,好像是在等黎耀辉回家,但是他不会回来了。何宝荣没有家,所以他可以在外流浪,了无牵挂,那个曾经会等他回家的男人也离他而去,他是孑然一身的。何宝荣具有典型的表演型人格,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黎耀辉全部的爱与包容,但却忘记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承受底线,而当他变得歇斯底里后,本就所剩无几的爱情便全部随风消逝,剩下的只有恨意与无奈,而这也是二人作别之时。
张宛这个角色的安排,在很多影迷看来是个败笔,甚���有人认为张宛这一角色使张震的形象显得不那么讨喜,但黎何二人失败的爱情真的就完全是张宛造成的吗?我想,张宛只不过是矛盾爆发的催化剂。黎何二人本身性格上就具有巨大的差异,黎耀辉沉默寡言,遇到问题并不会主动沟通,只是漠然在原地等何宝荣一次次的“回归”;何宝荣自负放肆,认为黎耀辉会永远在原地等他,却忘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这句至理名言放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张宛,还会有别人介入二人的感情中。张宛在一定程度上让黎耀辉清醒过来,他想将自己的遗憾与不快乐留在灯塔的愿望也促使黎耀辉独自前往大瀑布,黎耀辉最后选择同自己和解,他对何宝荣爱情的放手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解脱,他最后选择回到香港,回到家中,也是将张宛视作自己的“例子”。
有人说,王家卫没有给何宝荣一个结局,在我看来,这便是何宝荣最好的结局。他在影片的最后抱着黎耀辉的毯子放声痛哭,本就如同浮萍的他在这一刻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归宿与依靠。他的生活很有可能是继续与男人厮混,继续放逐自我,继续流浪,但是他的心里却永远会有黎耀辉这样一个缺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无家可归,香港与布利诺斯艾利斯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不过都是流浪的“异乡人”。当画面定格在黎耀辉的那间出租屋内,这份淡淡心酸后的意犹未尽能够使观众有更多的联想。
《春光乍泄》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讲述同性的影片在很多地方如果换作是女性角色,一定会有不同的处理与理解,同性本就更为敏感脆弱的性格在影片中有几处体现得十分恰当。比如上文中提及的当黎耀辉看到何宝荣与外国人激吻时,如果何宝荣是女性,我相信黎耀辉或许会选择“冲冠一怒为红颜”,即使失败,至少也是一种雄性气概;如果是为一个滥交的男人争风吃醋,恐怕沦为他人的笑柄。另一处是当何宝荣执意要拿回他的护照时,男女在感情中扮演的更多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但对于同样具有征服感的何宝荣,他无法忍受被黎耀辉私藏在家中的行为,最后愤怒地离去。男人之间的愤怒往往会通过肢体冲突体现,在影片中,黎耀辉与何宝荣多次大打出手,二人的肢体动作虽然显示自己极度的愤怒,但落下的拳头却依然是相对轻柔的,或许这也体现出二人内心的不舍与无奈;对于异性而言,男女体格上的差异以及传统观念中“好男不和女斗”的思想使得男女之间遇到矛盾时更倾向于通过争论、吵架的方式来发泄。
近��来《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四个月亮》《爱在末路之境》等同性题材电影的热映体现出世界范围内对LGBT群体的高度关注,但是当我们回到1997年的香港,同性的题材还是十分前卫的。LGBT群体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爱情是不分性别、年龄(恋童癖除外)与种族的,正是由于世俗的偏见与来自不同方面的伤害,很多LGBT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在现今的中国,LGBT早已不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但是大众传媒却始终避讳提及LGBT群体的权利、生存现状与心理健康,甚至Bilibili在审核视频时不允许出现同性亲密镜头的片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对LGBT的歧视,而我们也同样需要努力推动社会的公平发展。
为什么整个社会对同性恋情具有如此大的恶意?首先在于,我们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的统治之下,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形成了“社会共识”,当男性想要跨越这样的社会共识进入“女性角色”时,他是会被男性群体歧视并抛弃的。其次,改革开放距今不过40余年,这些“非主流”的思想在很多人眼中是西方文化的糟粕,父母辈的思想开化程度自然是不如现代年轻人,同性恋的社会接受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社会学中性学与伦理学在中国依旧是较为新兴且先锋的学科,文化学在中国依旧是缺失的,社会普遍对酷儿理论理解程度不够,同时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发展的差异使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偏见。最后,部分同性恋者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将自己视作“弱势群体”,并以此获利,在互联网上发布仇恨言论(包括代孕问题、“同妻”问题以及仇女倾向),一些还并不具有成熟三观的青年逐渐两极分化,一部分无脑支持同性恋,另一部分逐渐“恐同”,这对同性恋群体是极大的伤害。
在我看来,爱情始终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中,周遭的环境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的一个同性恋朋友曾和我说,倘若世界能对他多一些善意,倘若他的父母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怪物并且强迫他去看心理医生,或许他会活的更开心一些。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他与我又有什么差别呢,倘若要以一个人的性向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这样的评判标准本就是极度不客观的,我们谁又是真正“正常”的呢?我想,如果���能理解,也请抱有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
缺乏安全感的爱情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世俗的眼光与流言蜚语都是杀人的利器,两个本就敏感的人活得小心翼翼,无法得到认可,只能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而当飘零至他乡,矛盾与冲突让本就伤痕累累的二人失去了信任感,爱情成为桎梏,有人想逃,有人却想留在原地。我想多年之后,当黎耀辉与何宝荣再度回想起布利诺斯艾利斯的那段曾经浓墨重彩、春光乍泄的经历,会不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恍惚:这一切都曾真实存在吗?
我想,布利诺斯艾利斯,不过是存活于春光中的一场梦罢了。
[1]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J].语丝,1926(47)
0 notes
Text
無法複製的一道菜
藝文
世界副刊

楊秋生
1月&2月徵文:有故事的一道菜) 2023-01-30 02:02 ET
一直以為母親是不會做菜的。
出生官宦世家的外婆,嫁給外公的時候,帶著貼身丫鬟和廚娘作為陪嫁,母親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裡長大,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她不會做菜,似乎是極自然的事。而母親嫁給父親後,父親事業如日中天,家裡有數人伺候著,哪裡需要母親洗手作羹湯?
父親倉促來台,分文未帶,家裡環境相當緊張,父親捨不得母親做家事,仍僱了位阿婆幫忙洗衣燒飯。直到我出生之後,家用實在太緊,這才打住。照理當時父親長年駐紮金門,在沒有幫傭的情況下,家裡每件事情都是母親親手料理,包括六口的一日三餐。對幼兒時期發生的事情有著超強記憶的我,可以像一千零一夜每日一個故事如數家珍地講給大家聽,卻不知為什麼對於過往日常三餐吃些什麼,卻毫無印象。
我五歲���年,家裡從台中搬到台南,父親堅持餐桌一定要買十二人座的大圓桌,中間還要有個大轉盤。我對擺在大圓桌上面的食物開始有印象,已經是兩年之後,那是父親從軍中退下來,親手掌廚開始。
父親對燒菜特別有天分,吃過的菜只要他喜歡,一定能夠複製出來。他為人海派又好客,家裡經常高朋滿座,每道菜都是他精心設計的獨家私房菜。他燒菜燒出名來,不知多少人上門送禮,就只是為了能夠有機會來我家吃上一頓聞名遐邇的「將軍宴」。
母親身體一直不好,父親捨不得母親做家事,即使家裡請客,從買菜、洗菜、燒菜到洗碗,都是父親一手包辦,不讓母親插手。我懂事後,最多也只是在旁邊接手洗菜、切菜和洗碗等雜事。
記得有一天母親跟父親說,她這輩子都還沒有管過帳,能不能夠讓她管管看?
父親一口答應,說讓她管一個月試試看。
第二天早上大約十點半的時候,忽然聽到母親呼喚我們,說:「大家快來呀,看看我做了什麼好吃的東西給大家吃?」
我跑到餐廳一看,餐桌上擺了一個好大的不鏽鋼盆子,盆子裡頭裝滿了色澤漂亮的去殼蝦。
「這是我做的,你們盡量吃。大家就當點心來吃,不算正餐喔。」母親笑嘻嘻地說。
我們五個孩子圍坐餐桌,連筷子都來不及拿,五隻手伸進盆子裡抓起蝦就吃。當時覺得那蝦真是好吃,全然沒有想到母親是用什麼方法做的,調味鮮香,清爽美味,口感恰到好處,既不油也不膩,真是鮮美極了。在自稱「菜龍」與「菜虎」的兩位姊姊帶頭下,那一大盆比酒席上十二人份的量還多上好幾倍的蝦,轉眼就被我們吃光了。啊,原來母親不但會做菜,手藝也極精妙。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母親又端了一大盆子的醃黃瓜上桌。那醃黃瓜較之前一天的蝦,滋味毫不遜色,當然,又是被五隻手瞬間一掃而光。
第三天,換成一大盆酸筍,甭說那滋味有多迷人了,自然又是盆底朝天。
就這樣,一個禮拜之後,父親攤開帳本對母親說:「讓妳管家的結果,妳可是一個禮拜就把一個月的菜錢預算都花光了呢。」
母親心服口服地把掌管大權交了回去,從此以後又回復到之前父親買菜掌廚的日常。
父親菜燒得好,又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錢燒出最美味的菜來,我們經常吃得心滿意足。母親那個禮拜曇花一現的精妙手藝,很快地就淡出了我們的記憶了。
我後來移民美國,父母隨後也跟著移民美國。我懷孕時,一天從醫院回來,母親興沖沖地對我說:「中飯我煮好了。」我走到餐桌,只見盤裡一條蒸得漂漂亮亮的鹹魚,旁邊鑲著兩枚完美的荷包蒸蛋。我先生一見大呼:「鹹魚蒸蛋,我最愛吃的。」
原來母親愛吃鹹魚。
我這才意識到我對母親了解得那麼少,她喜歡吃什麼似乎從來沒有人關心過。我想起母親管帳那個禮拜的鮮蝦、醃黃瓜和酸筍,似乎明白了裡頭盡是母親的愛好和鄉愁。
父母親移民美國之後,照例還是父親掌廚。但母親愛吃魚,對於燒魚,父親似乎僅限於紅燒黃魚,自此燒魚成為母親的專利。每次去看望父母,母親多半希望我們留下來一起吃飯。母親的紅燒魚外香內嫩馥郁美味,舉箸大快朵頤之時,我似乎回到那個無憂年代,只顧著吃,從來沒想到問母親如何燒出這麼美味的魚來。
被父親稱讚菜燒得不錯的我,幾十年來一直不停地自我挑戰,開創出許多私房菜,家裡也經常有朋友來訪,每每吃得賓主���歡。母親尤愛吃我做的菜,有時吃得高興會說「我還要再添一碗飯」。我發現,我似乎走著和父親一樣的道路,寵著母親,做她喜歡吃的菜,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問過她:「你有什麼想吃的菜嗎?」也許,在她的心底,那盆鮮蝦是她的最愛。
近年來不知是不是年紀漸長的關係,我變得敏感而脆弱,總不自覺地懷念起父母還健在的日子,一幕一幕的歡樂時光,總在我毫無防備的時候蹦出來。經過歲月的沉澱,那一盆鮮香利爽的鮮蝦,在腦海裡益發甜美,使得我費盡心思想要複製。然而我這雙被文友稱為像魔棒的巧手,始終複製不出來記憶中的滋味,母親的鮮蝦遂成為絕響。
看著窗外屋簷滴落的雨珠滑過窗戶,彷彿一串串眼淚,母親喚著我們吃蝦的面容仍清晰如昨。我已分不清懷念的是母親那道菜,還是母親寵著我們的心?抑或是濃得化不開的鄉愁?(寄自加州)
0 notes
Text
第七場 愛情的腳步
透過臭小孩的貢獻(想不聽都不行),本日收獲︰隱藏性情敵,高志群一枚。
稍早的時候,看見那兩個人有說有笑地走在一起,臭小孩突然從他身邊冒出來,說他們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認識很久很久了。
他才不在意,反正曉寒貝現在是他的,時間不是問題。
哼了哼,很大度地繞過去打招呼,認識認識,教臭小孩學著點,什麼叫男人的風度!接著,那兩個人聊起一些小時候的事,他被晾在一旁,插不上嘴,自己識相地走開,讓好久不見的老朋友去寒暄,別佔布景當人形道具。
約莫中午時,高志群過來吃飯,兩人又聊了起來,他湊過去刷一下存在感,但因為聊的是育幼院裏蔬果供給的相關事宜,也沒他插嘴的分兒,於是再度默默消失畫面中。
臭小孩又晃過來,說志群哥對育幼院很照顧,就是那個傳說中的愛屋及烏什麼的。
哼,愛屋及烏他也會呀,信不信他可以「很、疼、愛」這只臭小表?!
他咬牙,陰沈地想。
再到下午時,有點想念,想找曉寒寶貝親親抱抱一下,臭小孩簡直像鬼一樣,N度由他身後飄出來,悠悠地說︰「曉寒姊去蔬果行了。好像說有什麼營銷方面的問題要請教她吧,姊很強的,如果不是去楊總那兒上班,現在應該是蔬果行的老板娘了。」
「……」他懷疑,臭小孩在他身上裝了衛星定位吧?怎麼走到哪都能看到他?
他有點搞不太清楚現在是啥情況,別說虞曉陽不懂這個就叫「挑撥離間」,陽陽臭小孩太早熟了,現在要耍呆萌裝天真似乎太晚。
那,他究竟是有多討厭他?要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必殺技攻擊?
夜闌人靜。
楊叔魏坐在草地上,身前環抱著佳人,享受蟲鳴星空、美人在懷的愜意時光。
「寶貝——」輕輕搖晃,親昵廝磨,偶爾偷幾個輕柔繾綣的吻。
這會兒,沒有高志群,也沒有老酸他的臭小孩,只有兩人世界,身心舒暢。
「嗯?」她低低哼應,柔馴地背靠著他,任由他將臉埋在頸間,纏綿拂吻。
楊叔魏含吮小巧女敕白的耳垂,模糊抱怨︰「臭小……我是說曉陽,他到底為什麼要討厭我?」被排擠的感覺好憂傷。
「嗯?」虞曉寒由迷蒙情韻中稍稍回神,撐開眸。「有嗎?」
「有啊。」他把今天的事說了一遍。
不是他在自誇,小魏子名號殺遍天下無敵手,向來只有被喜歡的分,很少被人討厭得這麼徹底,他究竟是哪惹到這尊小表?
她愈聽,嘴角不住地揚高,最後忍不住掩唇發笑。
「真高興我娛樂了你。」他酸了句。
「不是,曉陽是在跟你示好。」
「謝謝你喔。」好特別的安慰,他這輩子沒見過這種示好法。
「真的,他只是不會表達。」曉陽不是那種有城府心計的孩子,真討厭上了,不理會、或當沒看見就好,真正不感興趣的人,他不會費心去搭理,就像楊叔魏剛來時,雙方根本連話都說不上兩句。
或許是想試著認識這個人?跟他找話題?提供情報,表達「我跟你一國的」?又或者也順便警示他︰我姊很搶手,你要珍惜一點
總之不會是負面的意思。
「……」楊叔魏實在不知該擺出什麼表情才好。
被人沿路射了一身的箭,血條狂掉,然後才發現,對方是在追著說……哥哥我喜歡你!
吐血三升都有!
「他需要上人際關系課程!迫切地!」
虞曉寒仰首柔柔地吻了吻他下巴,幫他補血。「我想,他應該也只是想表達他的愛屋及烏。」
「我謝謝他!」楊叔魏沒好氣道。
丙然十歲就是十歲,再早熟還是只有十歲,有孩子的憨傻呆萌,不該把成人世界裏的復雜心計套在他身上。
說歸說,他還是想起自己提這件事的原因。「跟你商量一下,我覺得臭……小陽陽資質很好,我想好好栽培他,他比較聽你的,你出面跟他談談看?」
虞曉寒挑眉,微訝地看他。「你覺得他討厭你,你還想栽培他?」果真M體質嗎?
「這是兩回事。」一個可以成材的小樹苗就在他眼前,而他也有資源,為什麼不好好灌溉,讓他m壯?
她回眸,迎上他的唇,淺淺吻了記。「謝謝。」她知道,他也在愛屋及烏。
四片唇親密拂蹭、輕啄,額心抵著她,忽而失笑。
「怎麼了?」她揚睫,眸心染上淡淡情韻。
只是忽然覺得,他們好像老夫老妻,在操心小孩的未來與教育。
這種感覺,還不賴。
他沒多言,傾前深吻住她,撩起屬於情人間,獨有的旖旎濃情。
「寶貝,」他嗓音微粗,一臉渴求。「我想做。」
「不行……」在中載浮載沈的她,吐出微弱拒絕。
這裏人太多,連房間也隨時會有人進出,昨晚就被打斷過。
「可是我想。」掌心挲了挲她後腰。度假不就��要睡到飽、做到爽嗎?他們都好幾天沒那啥了。
男人不斷地蹭她、舌忝她、模她,以性感無比的嗓音誘惑︰「用你最喜歡的姿勢……」
「……」意志不甚堅定地動搖了一下。
「記得嗎?像上次那樣……」在她耳畔輕輕呵氣,引誘她腦海勾勒出曾經愉悅無比的畫面。
「……」低低地、微弱地吐出聲︰「……我知道一個地方。」
***
這太瘋狂了。
向來理性的她,居然跟著他一起胡來,開車來到無人的海邊,但是當他用挑逗的眼神,引誘她坐到他身上時……
不後悔。如果墮落的感覺,能得到如此甜美的果實,她不後悔沈淪,在那雙黝黑性感、深邃無際的黑眸底下,一同沈入深淵。
他?手,指月復撫過那被薰染、微帶媚意的眼角,位於心髒的地方,像被什麼牢牢抓攫,沒來由地一陣抽緊。
好像,就是某天夜裏忽然醒來,看著在他懷裏沈睡的臉容,然後發現心房一緊,那一刻他就知道,這是愛情。
他愛上這個女人了。
他不嘲弄愛情、也不褻瀆愛情,他只是,一直都不認識愛情。然後有一天,愛情的腳步悄悄來了,走進他心裏,找到最柔軟的地方紮根。
他才發現,原來愛情能帶來的,不是只有在大哥身上看到的那種愁緒與煩擾,它是雙面刃,有痛,就會有樂;有悲,也會有喜。
愛情,讓人如此快樂,光是想著那個人,心靈便能充盈著滿滿的喜悅。他從來沒嘗過這種滋味,光是疼著一個人就滿足,看著她笑,自己也會揚起嘴角。
「曉寒,」我的寶貝。他輕輕喊,心房暖甜。「你是我的。」
「嗯……」她哼應,不知是回應他的話,抑或只是本能。
身體相連、糾纏,感受著對方最細致幽微的情緒脈動,如此親密,如此甜蜜,原來,這才叫。
有愛,才做得出絲絲縷縷、入心的纏綿。
餅後,松懈下來,軟倒在他懷中。
他收緊臂膀,牢牢地,圈鎖住她。
她是他的。
青梅竹馬、蔬果行老板什麼的,都滾一邊去,此刻佔據她身心的,是他。
這或許,就是他今晚非要誘拐她、抱抱她的原因。
他用力地,吸吮她,在紅潮未退的頸膚啜出一枚紅痕,珞下屬於他的印記。
「寶貝,你知道嗎——」他柔緩地、催眠似地在她耳邊吐聲。
「嗯?」
「青梅竹馬、海枯石爛、情比金堅什麼的……都是騙人的,你千萬別傻得去相信這種鬼��。」
「……什麼?」她一蔣沒模著頭緒,感官泰半還沈浸在酥軟余韻中,腦子暈乎乎像團棉絮。
「你不要不相信,這是有市調數據的,情變分手的情侶中,有六十八趴都是青梅竹馬—起長大的。」什麼鬼數據,當然是弧?不用錢,不過某人說來臉不紅氣不喘,擺出一副學究專業貌。
不是說男人做完愛後最好拐,思考能力趨近零?女人應該也差不多吧?趁現在!
「你想想看,同一張臉看久了,能不膩嗎?有沒有道理?」
她好像……有點聽懂了。
可是,還是好難理解,前一刻還熱情擁抱,他甚至還在她身體裏,卻已經在暗示她,沒有不會變的感情,同一個人,看久會膩……
她以為,應該還有多一點時間的,再多努力一點,讓他沒有時間看別人,沒有空隙淡掉……
他已經……開始淡了嗎?
她知道他心性不定,也做好準備,就算,結果不盡如人意。
「所以……」她恍恍惚惚,一顆心空晃得沒有著落。他究竟想跟她說什麼?
「所以現在看起來再怎麼正直有為好青年,都難保以後不會歪掉,你看那個八點檔就知道,那個什麼志群的有沒有,黑到洗不白,真的!」
二堂哥他是黑不了,但若要黑別人,那是沒在心慈手軟的。
他知道,在她心中,仲齊哥的地位不容撼動,那是她人生的光,無論如何會擱在心上,敬重、仰慕。
這個他不會、也爭不了寵,反正人家就是那道白月光,他很認分當牆上的血蚊子。可是那個什麼群的,就不用講仁義道德了,所有出現在他眼前的雜魚,全數消滅。
「志群?」腦袋一下轉不過來。為什麼會提到他?「關他什麼事?」
「對,不關他的事,所以你看我就好。」接得好順。
「我一直……都只看你。」
「嗯。」這樣就對了,完全照他的劇本走。
他很滿意,咧嘴給她一個大大的笑容,獎勵地啄她一口。「寶貝真乖。」果然後超好拐。
「那……你呢?」她惶惶然,問道。
「我什麼?」
「你……膩嗎?」
「當然不會。」嘿嘿,原來她也想拐他。可以唷,他可以裝傻給她拐。「曉寒寶貝賞心悅目,就算變成黃臉婆,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黃臉婆。」
所以……他沒膩。
微慌的心,落了地。
她傾前,輕吮他的唇,溫的,一如以往,輕憐蜜意地蹭她唇心,對她的熱情,很立即地回應在她身體裏,滿滿撐脹著她。
「再來一次?」緩緩蹭動,摩挲她。
「嗯。」後半夜,她完全確定了,這男人對她的狂熱與興致,不曾稍減一分。
後來,虞曉寒前思後想,思緒理順了,總算弄懂他說那些話究竟是哪根筋拐到,而楊叔魏卻一輩子也沒發覺到,那晚要黑別人,卻差點把自己給黑掉這件事。
(阿彌陀佛!天公疼憨人,笨蛋的福澤總是比較深厚)
***
假期的最後一天,楊叔魏收好行李,出來找虞曉寒。
「姊去院長室了——」背後靈晃出來,悠悠地發聲。
他回頭瞄了一眼。
臭臉小孩依然很臭臉,但是經過曉寒給他突破盲腸後,他心裏多少有點底。
所以臭小孩真的只是想找話題跟他親近、熟悉一下而已吧?
看他無時無刻從他身邊冒出來,楊叔魏不覺有些好笑。
被人衛星定位的感覺……還挺妙的。
「欸,考慮得如何?跟我們住,或寄宿學校,選一個。」沒第三個選項。
難得有機會在臭小孩面前展現威嚴,他霸氣撂話,不容拒絕。
「寄宿學校。」虞曉陽秒回,連考慮都沒有。
「……」某人瞬間炸毛。「到底是有多不想看到我!」
真心換絕情。
曉寒寶貝根本是騙他的。
玻璃心碎裂,他要去告狀。
去院長室找人、不巧裏頭有客人,他不便進去打擾,裏頭的談話似乎差不多也到尾聲,他在門外站一會兒,便見曉寒開門送客。
看到門外的他,似乎一楞。
「來跟院長道別,感謝這幾日的招待。」他說。
虞曉寒點了一下頭,他越過她進屋,而她送客人離開。「朱先生請。」
與院長話別完出來,提著行李上車,這幾日混熟的大人、小孩出來送客,虞曉寒被叮嚀有空要常回來——當然,帶他一起。
兩人上車後,楊叔魏啟動引擎,看見虞曉陽?手,朝他輕輕揮了揮,細聲道︰「姊夫再見。」
他輕笑。「再見,小陽隞。」
臭小……好啦,其實也沒那麼臭臉,直到這一刻,細細玩味,愈想愈覺這小孩惹人疼,就像她。
初始,會覺冷漠、難以親近,但慢慢的,只要你有心,會發現他們冷硬表相下,那顆真誠柔軟的心。
他們,都有一種特質,讓人想起,便覺心頭發軟的特質。
可愛的小表。那小小聲、害羞無比的「姊夫」,把他心都喊融了。
回程路上,他愈想愈不妥,開始跟她碎念︰「小陽陽說他要住宿耶,才幾歲而已,裝什麼獨立?」十歲的孩子,被丟進宿舍,生活自理,身邊沒有大人關愛,缺乏家庭溫暖,會不會長歪呀?
「不行不行,你再去勸勸他好了,至少頭幾年跟我們住,等大一點,真的想要私人空間再住宿也不遲……」
虞曉寒���笑的眸瞅視他,放任他在那裏一會兒笑、一會兒皺眉,搖頭晃腦、自言自語。看起來,就是那種會把小孩寵壞的慈父類型。
欣賞夠了,她才慢悠悠地啟口︰「尊重他的意思吧。」
「你都不擔心?」
她搖頭。「不擔心。」
育幼院與學校,差別能差到哪?曉陽性子她了解,歪不到哪去的。他從小就是很有自覺的孩子,自主性與自我約束能力都比一般同齡孩子高許多,從不造成旁人的困擾,會選擇住校,應該是不想打擾他們的兩人世界,若勉強他,反而會讓他有心理壓力。
「好吧,那不然來談談你擔心的事?」
「什麼?」
「例如朱先生。」
「你聽到了?」
「一點點。」剛好聽到尾巴。「不用擔心,你把朱先生的聯絡方式給我,我回去找代書跟他談。」
「你要幹麼?」
找代書能幹麼?楊叔魏睨她,曉寒寶貝變笨了。「他要賣地,那我買就是了。」
「……」可以不要用市場買蘿卜的口氣說嗎?
他看得懂這眼神喔!「對啦,我財大氣粗。」能用錢解決的事,那幹麼不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掉就好?
「我不是那個意思……」她低噥。「只是覺得,你沒有必要……」
「有必要。」她的事,就是他的事。
她靜了靜,沒搭腔。
他本想回——就當是聘金好了。
但又覺得,那樣講好像逼她非嫁他不可似的,又吞了回去。
基本上各種言小浪漫路線他都不排斥來一下,只有那種富豪遇上落難女,以錢財強娶的橋段,他個人非常堅決罷演。
「仲齊哥能做的,為什麼我就不行?」曉寒寶貝好偏心。雖然他本錢沒仲齊哥那麼粗,但買下一塊地,讓孩子有個棲身之地,安心地在那裏成長,他還是做得到啊。
居然一臉被虧待的委屈表情……虞曉寒無言了好半晌,最後模模他臉頰。
他立刻又眉開眼笑。「就這樣說定了?」
「……」她根本什麼都沒說好嗎?不過說與不說也沒有差別,他已經勢在必行了。想了想,覺得自己還是應該說點什麼,卻挖不出適合字句。
「那個……原本的地主是個很好的人,一直都用低於行情的價錢把地租借給育幼院,我們都喊他朱爺爺。他過世前,說會交代他的兒子,可是朱先生繼承遺產後,並不打算遵從老先生的遺願,租約一滿,就……」
「不肖子孫,哪裏都有。我爺爺和柯老那一代,也是一同拚天下的好兄弟,可是上一輩的想��,下一輩誰鳥你。你看看柯志民那個樣子,我們就算念著爺爺那一代的交情,想容他他也容不了我們,兩家情誼早敗壞光了。」
「叔魏……」
「嗯?」
說東說西,其實想說的,只是一句︰「……謝謝。」
他回她暖暖微笑。「傻孩子。」
苞他,有什麼好謝的?
7 notes
·
View notes
Text
换妻换的爽
我��班后觉得好兴奋,兴奋得真快受不了。一进入屋,老婆阿美刚一打开客厅的电灯,我就从後一把抱住她,又硬又胀的老二往她的屁股沟里猛挺,一只手快速地揉着她饱满的胸部,另一只把她的头往後一扭,嘴巴对着她的香唇用力吻下去。
太爽了。虽然我们都还穿着衣服,但老二顶着软软的屁股肉的舒服感觉,还是一阵阵传过来。阿美的胸部是她的最大骄傲,三十四D,美丽的梨形,坚挺饱满,现在隔着她薄薄的上衣用力模揉,就好像摸着一团温热的棉花团。 我的嘴和老婆的嘴紧紧吻在一起,老婆的口内又湿又滑,两人的舌头相互搅拌,我吻到自己满嘴的酒味,和老婆唾液的微香,那种感觉就好像老二已经插进老婆的美穴中一样。 我上面用力吻着,下面则用力猛顶,按住老婆乳房的那只手,这时也很快向下伸,一把撩起老婆的迷你裙(干!老婆就是喜欢穿这种超短的迷你裙,让我看了,不想干她都不行),抠向老婆的屁股底沟,一下子就模到湿湿的三角裤底。 我用力抠了几下,老婆发出几声淫叫,但因为嘴巴被我吻得死紧,只听得见「哦┅┅哦┅┅哦┅┅」的淫声浪语。 我等不及了,一把拉下她的三角裤,让她露出光光的下部,同时用手猛地往她的阴部一抠,马上抠到满满的一把淫水,看来她也跟我同样兴奋。 在我还从背後抱着她,并且一手扶着她的头,让她回头和我亲吻的情况下,我单手解开腰上的皮带,让长裤落下,并且再拉下内裤,然後用脚把长裤和内裤一起踢到一旁,露出早已昂然挺立的阴茎。 接着,我把她的左腿往上一抬,让她的小穴外张,我怒涨的老二立即往她穴内一送,一根红热的阴茎插进春潮淫淫的温暖小洞内,又紧又暖的嫩肉紧紧包住我的阴茎,舒服得让我呼出一口大气,老婆更是狠狠地哼了一声。 结婚好几年,夫妻两人早已经干出默契来,只要兴趣一来,我们通常就是这样随地就干起来。老婆跟我一样冲动,稍加调情,她的小穴就会淫水满溢,让我的阴茎一插就进,然後就是疯狂的大肆抽插,老婆则是纵情相迎,两人干得不亦乐乎。 今晚去参加老婆专科同学安妮的结婚喜宴,���氛很好,同桌的还有老婆的另一位同学小莉和她的先生小高,大家都谈得很开心,我多喝了几杯,弄得心情很HIGH. 离开喜宴的饭店,在开车回家途中,我早已性趣大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伸向旁座的老婆,偷袭老婆的胸部,惹得老婆娇笑连连,但也一再警告我要小心开车。 好几次,只要一停在红灯前,我就一把将老婆搂过来,和她深情地接吻。 老婆的反应也很好,她陶醉地闭起眼睛,喉中还发出「哦哦」声,甚至还把手伸向我下部,摸到我硬梆梆的老二时,她忍不住说∶「哥,你好硬哦!」刺激得我真想停车,当场就干她个痛快。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老二也终於顺利插进老婆的小穴内,我开始用力抽插起来。这时候,我同时占据了老婆上下两个洞,两个洞同样湿润温暖,那种感觉好像同时在干两个女人。 这样干了约十分钟,虽然够刺激,但总是有点不顺。於是,我放开老婆,飞快剥下她的短裙、上衣和奶罩,她那完美的胴体马上赤裸裸地呈现在我面前。 老婆也没闲着,在我剥她衣物的同时,也解除了我全身上下的衣物。 来不及上床了,我抱着她往地板上一躺,紧紧压着她,怒涨的老二一刻也没浪费,马上再度插进她的小穴中,并且疯狂地插了起来。 老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出声,兴奋的她,立即惊天动地的叫起床来。 听到她如此淫声浪语,再加上酒气这时冲上脑来,我简直像疯了一样,硬挺的大鸡巴毫不留情地向着老婆穴内猛干,一下比一下重,让我觉得自己实在神勇无比。同时,两手也用力猛搓老婆的那双大奶。 老婆这下可真的爽歪了,脸上红潮如彩霞,一面喘气,一面叫个不停∶「哎呀,哥呀,干死我了┅┅哦┅┅哦┅┅」 就这样狂插猛干了好一阵子,我突然觉得老二一阵酸麻,再也顶不住了,我伸手紧紧抱住老婆,同时用力吻着老婆,下面则使尽全力往老婆小穴内一顶,只觉得已经顶到老婆的穴底了,我就用力顶着,一动也不动。 老婆也感觉到了,她几乎陷於疯狂状态,双手也紧紧搂着我,屁股则拼命向上抬,嫩嫩的穴肉紧紧顶着我涨得快要爆炸的阴茎,「哦┅┅哦┅┅哦┅┅」从她的喉咙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呻吟。 终於,我爆炸了,累积了几天的浓浓精液一下子射出,我痛快的绷紧全身肌肉,并且感觉到阴茎猛然抽搐了一下。 老婆的反应更是激烈,她死命地搂紧我,指甲深深陷入我背部肌肉。她穴内的嫩肉也跟着一阵���缩,把我的阴茎包得更紧。她同时使尽全力吻了我一下,然後,她的唇离开我的嘴巴,紧接着,发出一声高潮後的叫声∶「哦┅┅死了┅┅被哥给干死了┅┅」 高潮过後,我们两人还紧紧抱在一起,躺在客厅地板上。 过了好一会儿,老婆轻轻推开我,翻个身子,爬到我身上。她含情脉脉地吻着我,丰满的双乳贴在我胸前。老婆伸手到下面,轻轻摸着沾满我自己精液和她的淫水的阴茎,又开始用手轻轻套弄起来。 虽然刚刚才大战完毕,但看到浑身赤裸的��婆趴在自己身上,美丽的双乳贴着自己,她那柔软的小手又在轻轻拨弄我的阴茎,刚刚软下去的阴茎不禁又慢慢硬了起来。 老婆这时乐得又红了脸,她春情烫漾地说∶「哦,大鸡巴哥,你今天真的好强,一进门就把妹妹干得爽死了┅┅哎哟┅┅又硬起来了呢┅┅讨厌┅┅不行啦┅┅真要干死妹妹呀┅┅不行啦,会把妹妹干死的┅┅」看到老婆这样的媚态,我不禁又跃跃欲试了。 谁知道,老婆这时突然对我眨眨眼,狡黠地对我笑着说∶「其实,你今晚这麽兴奋,并不全是为了我,对不对?你是看到小高的老婆小莉的骚样子,很想狠狠干她一顿,所以,一回到家里就抓住我猛干起来。其实,你在干我的时候,心里有一部分是想着正在干小莉,是不是?」 听到老婆这麽一说,我不禁愣住了。 但我只呆了一下下,马上就恢复镇静,并且嬉皮笑脸地对老婆说∶「是吗? 是那样子吗?那你呢?你还好意思笑我?你刚才也够骚了,但也并不是完全为了我,对不对?你还不是在酒席上跟小莉的老公打情骂俏的?你才真想被她老公大干一场呢?还敢笑我?」 说完,我两手扶着老婆的屁股,用力往上一提,让老婆的屁股暂时离开我下面,连带地也使我那根再度硬起来的大鸡巴脱离老婆小手的掌握,接着,我屁股往上一挺,再把老婆屁股往下一带,「滋」的一声,大鸡巴不偏不倚地再度插入老婆那淫水横流的蜜穴中。 我先用力往上猛顶,让龟头着实顶住蜜穴的肉壁几秒钟,然後,我把老婆屁股往上提,接着,再往下带,就这样上提、下带地,老实不客气地使出我的「倒浇蜡烛」绝招,确实确实地干了起来。 真是受不了,竟然有这样骚的老婆,我前辈子一定是烧了数不尽的好香,今天才能如此干得尽兴。看到老婆在上头剧烈晃动着,一头长发飞扬,秀脸飞红,胸前两颗巨乳上上摇摆,乳波惊人,让我又爱又怜。 因为是第二次再干,而且酒意还未全消,所以,这一次干了十几分钟还没有射精的感觉,但看到老婆在上面这样子剧烈地骑着我,也实在很累,於是怜惜心油然而生。我放开老婆的屁股,两手往上一搂,用力把老婆上身往下一拉,让她紧贴在我胸前。 我热情地和她接吻,疼惜地说∶「妹妹,趴在哥哥身上休息一下,我暂时不把鸡巴拔出来,等一下再干。」 老婆红着脸,吻着我的唇。每一次,她那肉肉、湿湿的唇贴着我的唇,让我觉得就好像她的两片阴唇紧贴着我的唇。 她笑着说∶「你想干小莉?这其实不能怪你,小莉是我那一票高中死党中最骚的,当年不知迷倒多少男孩子。几年不见,现在样子更骚了,难怪你看得很睛都直了。如果不是有那麽多人在场,我看你呀,当场就上了。大色鬼!」老婆一语道破我心中的淫念,让我尴尬不已,不过,结婚这麽多年,老婆早就知道我有这个好色的毛病,尤其最喜欢别人的老婆。所以,尴尬归尴尬,我还是「嘿,嘿」笑了两声,屁股往上抬了一抬,老二快速地在老婆小穴内连插了两下,夹着淫水,发出「噗,噗」声。 冷不防遭到突击,老婆笑着骂了我一句∶「哥,讨厌啦,偷袭人家,要死了呀,说到你心坎里了吧,瞧你那麽乐。」 也难怪我乐。今晚我们夫妇进入喜宴会场时,马上就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我捧起她的脸,深情地吻着她。吻着,吻着,我开始冲动起来,两手顺势摸到她的屁股,胯下坚硬的老二往前顶。老婆赶紧推开我,红着脸说∶「哎呀,不行啦,哥,快走吧,快来不及了。」 到了喜宴会场的饭店,我美丽的老婆果然引起大家的注目,让我深感光荣。 「阿美!」突然传来这样的呼唤声。我和老婆转过头去,我眼睛再度一亮。 老婆阿美已经很亮丽了,而这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女人也同样出色。 跟老婆的短裙相反,这女人穿着及地的长长黑色礼服,充分展露出修长、曲线玲珑的美妙身材,礼服下摆是开高叉,露出她纤细的小腿,和一部分丰腴、白晰的大腿,而礼服上面的胸口则开得很低,可看到很大部分的丰满双乳。她是一头长长的秀发,整个给人一种神秘、秀气的美感,不同於一头短发和劲装的老婆阿美所展现的狂野美艳感觉。 「好呀,死小莉!是你!」老婆高兴地大叫,上前一把抓住那位丽人的手。 两人拉着手,高兴地抱在一起,又说又笑的,把我和那位美人身旁那位瘦高个子的男士抛在一边。 两位美人相互介绍了一下。原来,老婆阿美、小莉和今晚的新娘子安妮是专科时的同班死党。但三人从学校毕业後,就各分东西,再也没有连络。小莉回到她家乡高雄工作,老婆阿美和安妮则在台北就业。 婆和小莉两人久未见面,这下子一见面,马上讲个不停,直到入席时,两人还兀自讲个不停,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到我们落坐的位置。 而小高也一脸陶醉的神情,显然也跟我一样,难逃别人漂亮老婆的亲蜜攻势乡小高这家伙可真有艳福。特别是老婆的超短迷你裙,在坐下後,几乎可以看到她的内裤了。 妙的是,小莉在发现我几次在注意老婆那边的情况後,反而更亲热地向我靠得更近,也频频向我抛媚眼,大有和阿美一较长短的意思。 酒席的气氛很热闹,我们两夫妇都很High,不停地向对方敬酒。等到酒席进行到一半时,大家都有几分醉意了。阿美和小莉脸上都红红的,眼波荡漾,更显娇媚动人,动作也越来越大胆。小莉好几次偷偷在桌底下将手放在我大腿上,并且用指尖轻轻?过,像触电般的感觉传来,干!我的老二马上硬了起来,被紧紧包在裤子里,实在很难过,偏偏小莉又在这时候转过头来,故意朝我淫淫媚笑,害得我精虫上冲大脑,真想一把将她按倒在地,当场干她个天昏地暗。 再看看老婆阿美,她也显然同样春情发作,娇态十足。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也放在桌底下,而且正在上下移动,小高也跟我一样露出快要忍不住的陶醉表情。妈的,搞不好,老婆正在抚摸他的老二呢! 这时,新娘安妮和新郎前来敬酒。安妮看到两位好同学,高兴得挤到她们两人当中,热烈地敬起酒来。我站在一旁居高临下,眼中看到的是三位美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性感,而且个个都是一对豪乳,峰峰相连,乳沟深深,看得我差点就要大喷鼻血。 酒席结束,大家在酒店门口道别时,我已经性趣高到快要控制不住了。 想到这儿,淫兴再起,我用力抱着老婆,翻转过来,再度把老婆压在下面。 刚刚一直浸在老婆小穴淫水中的老二,因为得到短暂的休息,这时变得更硬更有力。於是,我老实不客气地用力干了起来。老二开始一下紧接一下地,快速而有力在老婆那满是淫液的美穴中抽插。 老婆立即感受到我老二的强大威力,乐得她又叫个不停∶「哦,哥哥,好老公┅┅你好硬好够力┅┅哦,太好了┅┅用力┅┅干死妹妹了┅┅哦┅┅又干进来了┅┅」 我实在插得太爽了。硬硬的老二在老婆那淫水涟涟的美穴里插进拉出的,不断发出「噗吱、噗吱」声音。由於阿美的小穴很紧,老二在拔出时,把她的穴肉也连带拉了出来,那种扎实的感觉,好像是一张小嘴紧含着老二不放,差点把我的精液也拉了出来。老二在拔出到将近穴口时,我再猛力插入,一下子就顶到阿美的穴底,龟头着实地碰着穴内的嫩肉,每顶一下,老婆就张开嘴发出一声「哎哟」,并且浑身抖了一下,把我抱得紧紧的。 看着老婆在我老二的威力下,被干得娇喘连连,淫声不断,一副十足陶醉的模样,让我感到男性无比的快感和尊严。 干着,干着,我突然想起今晚酒席上的小莉,她的风情万种和骚模样,以及她的小手放在我大腿上的那种触电感觉,让我不知不觉的把下面的老婆幻想成是小莉。 不知道小莉干起来会是什麽味道?会像老婆这麽风骚迎合吗?不管了,就先把老婆当成是小莉,好好干一场。 「小莉,我要干死你!」我一面在心里如此想着,一面更加用力地去干着老婆,想像成小莉正被我干得哇哇叫呢! 老婆在我下面被干得狼狈不堪,但显然也是乐翻了。她的反应也跟我一样热烈,热烈得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这让我突然起了疑心,搞不好,老婆也跟我一样,幻想着现在正在干她的,正是小莉的先生小高。看她今晚在酒席上和小高眉来眼去,这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不管了,就当她真的想着小高,反正我也想着小莉,大家扯平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实在干得太爽。 我收拾起胡思乱想的心思,再度专心打起老婆的「洞」来。先是一抽一插,再来就是用九浅一深的插法,最初是缓缓的九次抽插,插得不深,也抽得不很出来,但在九次浅浅的抽插,让老婆觉得并未觉得很尽兴,而心痒痒时,我却突然用力狠狠地、深深地向前一插。 在前九次浅浅的抽插时,我的大鸡巴一次又一次地在老婆紧密的小穴里来来回回,刮动她的穴肉,老婆舒服地一次跟一次的随着我的抽插动作,发出「哦,哦,哦」声,等到九浅之後的那一次用力一插时,她马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叫∶「呀!」接着就是歇斯底里似的淫叫声∶「坏死了┅┅讨厌的哥哥┅┅吊人家的味口┅┅插得人家快受不了┅┅又那麽用力插┅┅小穴都被你插破了。」好美的一个夫妻淫荡之夜。 一个星期後的星期五,我在公司加班到晚上七点,临下班前,突然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老公,我现在在福华饭店中庭,和一位朋友在一起,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我很快赶到福华,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老婆所说的那位朋友,赫然是──小莉! 小莉在一家新银行上班,所以穿着银行那种套装式的深蓝色制服,合身的剪裁,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和美好的身材,十足是个美丽的上班制服女郎,别有一番风情。 原来小莉的老公小高是位电脑新贵,两人虽然是在高雄结识、结婚,但婚後不久,小高的电脑公司搬来台北的内湖工业园区,两夫妇就举家北迁,小莉也在台北就业。老婆在那天酒席上与小莉久别重逢後就恢复了连系。 这一顿晚餐吃得十分愉快。在优美的气氛中,面对两位美女,真让我不喝酒也醉,更何况我们还点了一瓶���酒。美酒、佳肴、美女,人生还复何求。 小莉和老婆刚开始时还聊些学校回忆及工作上的事情,但随着气氛越来越轻松,两人的聊天内容也转趋轻松,但後来越聊越开放大胆,最後甚至聊起彼此的床上趣闻。 令我感到嫉妒的是,从小莉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她对她老公的床上表现是很满意的,频频称赞老公的床上技巧。 老婆自然不甘示弱,马上当着小莉的面大力替我宣传起来,说我在床上有多勇多猛,常常搞得她求饶不已。 「他呀,先天本钱够,又大又粗,又有爆发力兼持久力,每次都让我满意极。 本文最早由——777mi.net发布 老婆如此说。 我当然得意不已,小莉可是听得羞红了脸。 老婆还不放过她,竟然身体向前倾,嘴巴凑到小莉面前,捉狭似地低声对她说∶「有机会,你也试一试就知道了。」 小莉脸脸更红了,轻声地骂了老婆一声∶「死阿美,那有这样推销自己老公的?就只有你老公行呀?有机会也让你试试我老公的厉害。」阿美随即回答说∶「好呀,我正求之不得呢!」说完,两人笑成一团。我则乐得清闲,喝着红酒,看着她们两人说说笑笑。 突然,老婆的手机响了。 「喂┅┅是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接完电话,老婆抱歉地对着我和小莉说∶「对不起了,公司打电话来,有急事,要我现在回去处理。我先走,你们留下来吃完饭,再聊聊天。」老婆在网路公司上班,公司是二十四小时服务客户的,像这样临时被找回公司处理急事是常有的情形。 老婆临走前,又交待我说∶「老公,等一下你就送小莉回去,她住内湖。」接着,她背对着小莉向我眨眨眼,露出神秘的微笑,然後就快步离去。 老婆走後,剩下小莉和我,我们两人对望着,一时觉得有点尴尬,不知道让该说什麽。我举起酒杯,向她敬酒,两人同时各喝了一大口酒。 酒一下肚,气氛开始轻松起来,我们很自然聊起天来。原来小莉还满健谈谈的,不停地告诉我,她、阿美和安妮(就是新娘子)当年在学校里的风光往事,她们三人被称为「×专三朵花」,当年不知迷倒多少男孩子。 小莉很快恢复先前和阿美谈笑风生的神采,红红的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更显风情万种,害我一直盯着她看,竟然一时忘了回答。 「你怎麽一直盯着人家看,一句话也不说?」小莉忍不住发出娇嗔。 「我想起了那天酒席上的情形,我一直忘不了呢!」我大胆地挑逗。 小莉一下羞红了脸,低下头,娇羞不已地说∶「你好讨厌,人家那天酒喝多了嘛!你干麽记着?���要拿出来说。」 不知不觉的,一瓶红酒喝完了,看看时间,竟然已九点多,於是我们买单离开福华,由我开车送小莉回内湖。 走出福华後门,准备走向停车场时,小莉突然一个脚步不稳,差点跌倒,还好我及时一把将她抱住。抱住她後,我马上感受到一股冲动,又香又软的女性胴体紧贴在怀里,带给我一种无法言谕的快感。我不但没有立即放开她,反而把她搂得更紧。 小莉抬起头来,仰望着我,脸红红的,两眼水汪汪,香唇微张,呼吸急促,神情妩媚。然後,她缓缓闭上眼睛。 这是邀请的表示了,我不是傻子,於是我低下头,吻上她的香唇,但只是轻轻一吻,马上就分开了,因为这时候正好有一大群人经过。 小莉夫妇的家在内湖工业区附近的一个新社区,是一栋雅致的两楼小别墅,倒很符合小高电子新贵的地位。 我把车子停在她家门口,很自然地跟着小莉走进屋内。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刚一进门,打开客厅内的电灯後,小莉马上回转身抱住我。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这时候竟然有点温热,显然她已经春情荡漾。我用力回抱她,同时热情吻着她。她微微张开双唇,我的舌头立刻趁虚而入,滑入她口中,和她的香舌纠缠在一起。 我双手往下滑,在她那又软又滑的臀部上摸索着,然後我老实不客气地把手伸到她胯下,摸起她的小穴来。虽然还隔着裤袜和三角裤,但摸着摸着,我感觉到她���儿已经有几分潮湿,她的呼吸这时开始急促,但由於嘴唇被我紧紧吻着,因此,她只能从喉中发出断断续续的「嗯,嗯」声,她的身体更热了,甚至微微发着抖。 面对如此热情的可人儿,实在不需要再客气了,我摸索着找到、并拉下裙子的拉炼,接着用最快的速度用力扯下她的裙子、裤袜和三角裤。小莉也发挥最高的配合度,包括抬起自己的脚,踢掉被我扯下的裙子和三角裤,同时还主动解开我的皮带,拉下我的长裤和内裤,露出我那已经昂然挺立的大鸡巴。我也学她抬起脚,一脚把自己的裤子踢开。 我们继续紧紧抱在一起,疯狂地吻着,但我们开始移动身子,向着长沙发移动。 我们一起倒在沙发上,我把小莉压在下面,分开她的两腿,大鸡巴对着她的小穴用力一挺,一下子就插了进去。 「哎哟!」小莉发出一声惊呼。??我一点也不浪费时间,马上用力抽插起来,而且都是每次用力插到底,再拔出一点,再用力往内插。 因为情绪被挑到最高点,所以,我是疯狂地狂插猛抽,而小莉也是疯狂而热情地迎合着。 小莉和老婆阿美都很美,但两人不同型。老婆长得比较丰满,是狂野型的,个性开朗奔放。小莉则比较内向,身材略瘦,是修长型。 两人外表和个性上的差异,我早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直到现在,我把老二插到小莉穴内後,我才能够进一步比较她们身体这一部位的不同。老婆的小穴丰美多汁,肉肉的,淫水来得又快又多,老二插在里面,觉得就像被她的嘴巴含着,肥肥的穴肉紧包着老二,源源不绝的淫水,就像口中的香津,让我的老二抽插起来十分滑顺,却又有着紧密的快感。 小莉的小穴则比较秀气和瘦削,穴肉和淫水也没有老婆多,所以老二插进去後,先会有着很紧密、且略感乾涩的感觉,但老二被她的小穴包住的感觉更为强烈,带来的刺激感也更尖锐,也因为如此,小莉被抽插时的感觉也显得比阿美敏锐。所以,在我刚才猛力一插时,小莉一定感到带点乾涩和刺痛的刺激,她才会发出那「哎哟」的呼痛声。 但在我紧接着的狂抽猛插下,她的淫水快速排出,马上进入佳境,紧紧、滑滑、瘦削的穴壁包着我的老二,带给我无比的快感。而我粗壮的老二因为被它的小穴包得紧紧的,因此,老二进入与退出时,也会紧紧拉动她的穴壁,相信一定也让她尝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感与快感。 在这儿,又可以看出她和老婆的另一个不同点。 老婆阿美是开朗狂野型的,因此,她在被干得舒服时,会忘形地大呼小叫,淫声浪语不断,「哥哥」、「妹妹」喊个不停,让我听了性趣大增,干得更为舒服。小莉则不同,尽管我感觉得到,她被我这番猛然而来的强攻猛打,干得极其痛快,但她还是咬着牙,口中只发出「嗯┅┅嗯┅┅嗯┅┅嗯┅┅」的呻吟声。 不过,她这种极力忍耐的呻吟,再加上她陶醉的神情,别有一番含蓄的美感,同样刺激着我,激发我更大的爆发力,更加对着她狂插猛抽。 「嗯┅┅嗯┅┅嗯┅┅哦┅┅哦┅┅嗯┅┅」小莉继续发出扣人心弦的低声呻吟。 我把小莉紧紧压在沙发上,一连狂插了几百下。然後,我站起身,抓住小莉修长的两条光溜溜的大腿,把它们抬起、分开,让小莉的屁股暂时离开沙发,悬空,我的老二再度凶猛插入,再次狂插。这种姿势,让我插得更深入,龟头下下直抵她的子官口。 这让小莉兴奋得几近疯狂,那「嗯┅┅嗯┅┅嗯┅┅哦┅┅哦┅┅嗯┅┅」的呻吟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尖锐,好像哭泣一般。她兴奋得头部左右剧烈摇动,模样狼狈不堪,但也极其淫荡,更勾动我的男性本能,干得更用力。 这样子站着干了将近百下,我累得再度跌落在沙发上,恢复原来的姿势,又一连干了几十下。小莉这时候已经发不出呻吟声,只是急速地喘气,嘴唇泛白发冷,阴户猛力往上顶了几下,接着就停住了,看样子,她快不行了。 而我也感到老二开始出现酸麻感,我把嘴巴凑到小莉耳边,气喘吁吁地说∶「小莉,我要射出来了┅┅让我拔出来,射在外面,好吗?」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小莉竟然猛烈摇着头,口中发出「哦哦」声,两脚夹住我的屁股,阴户往上一顶,让我的老二紧紧抵住她的穴顶,好像怕我真的把老二拔出来,她的双手更紧抱着我上身不放。 受到这样的鼓舞,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使尽全力,往她的小穴又猛插了十几下,然後,脑中轰然一声巨响,老二一阵膨胀,然後,精液夺关而出,「噗吱、噗吱」地射向小莉的花心。 小莉发出「呀~~」的一声长呼,两手两脚像只章鱼似地紧紧缠着我。 我们紧紧抱在一起,这一波的激烈做爱,累得两人几近虚脱,谁也说不出话来。我们就这样抱着,躺在沙发上,感受彼此的柔情蜜意,倾听彼此激烈的心跳声。 不知过了多久,小莉才幽幽的吐出一口气,无限娇羞地说道∶「我差点死去。」接着,她笑着说∶「阿美说得没错,你真的很有爆发力呢!让人家来不及准备就遭到你的突袭。」 我觉得很得意,说∶「谢谢你的夸奖。但你忘了阿美说的,我也很有持久力!」我想了一下,接着说∶「这次偷袭,共干了半小时哩!」小莉「咯咯」地娇笑不已,她说∶「你倒很谦虚,其实呀┅┅」她爱怜地摸摸我的脸,说∶「你这一下就做了将近一小时呢,很厉害哦!」她离开沙发,亭亭站着。 我们一进屋里就干上了,当初只来得及脱下我的裤子和她裙子,因此,她现站在那儿,上半身还穿着她的套装上衣,白衬衫头几个钮扣敞开,露出白白的趐胸,一头秀发乱乱的,下半身却是赤裸的,修长的两条大腿白得耀眼。她先伸手挽挽一头散乱的秀发,但手一动,马上就有白白液体从她的两腿间流下来,原来是我刚刚射进去的精液呢! 小莉把长长的秀发挽成一团盘在头上,接着,她依序脱下套装外衣和衬衫。 於是,小莉那曼妙的胴体就完全呈现在我面。豪乳、细腰、丰臀和修长的大腿,再加上她因为兴奋而红红的脸孔,以及正一点一滴从她小穴中滴落到地板上的我的精液。 老天!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一幕,那真是一幅超级淫荡画面。 小莉朝我媚笑着,伸出一只手来,一把将我从沙发上拉起来,并且撒娇似地骂我∶「还躺在那儿发呆呀?一起去洗澡。」 我乖乖地站起来,小莉投入我怀中,一面替我解下领带,脱掉我的西装外套和衬衫(跟她先前一样,我也是下身赤裸,上身还穿着衣服),真是温柔到了极点。我则趁机揩油,一下子吻吻她,一下子又摸摸她高耸的双乳,惹得她娇笑不已。 到了浴室,小莉和我边洗边玩。我不断地搓洗她的双乳,她则不断把玩我的老二。在热水冲洗下,很快的,我又兴奋起来了,老二挺得高高的。 小莉替她自己和我涂满全身的沐浴乳,然後把我推倒在浴室地板上,她则坐在我身上,用她的阴部在我胸前搓揉,我伸手向上,老实不客气地抚摸着她的双乳。涂了乳液的乳房又滑又软,触感一级棒!小莉接着慢慢向下滑,她的阴部慢慢来到老二处,她的穴沟开始在我老二上滑动搓揉着。 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等到她的穴口滑到我的老二头时,我抬起屁股,顺势一挺,老二顺着泡沫很快滑入小莉的小穴中。 小莉的小穴里,这时又滑又温热,我的老二进入里面,好像泡在紧紧的温水瓶里,舒服极了。我双手往下滑,扶住她浑圆的屁股,老二开始朝上顶。由於有水又有泡沫,这样子的抽插极其容易,但也更刺激。 小莉被干得极舒服,在我上面开始呻吟起来了∶「嗯┅┅嗯┅┅哎哟┅┅哦┅┅哦┅┅」 浴室里蒸气弥��,温度很高,我和小莉都热得出了汗,尤其是小莉,她满脸通红,秀发蓬乱,不断滴着水,样子很淫荡,但也很吸引人。 看着这样的美人儿,我越干越有劲,一下比一下有力,干得小莉连呻吟也快要发不出来。 兴奋的小莉,这时突然疯狂起来,她猛烈前後摇动屁股,加快我老二抽插的速度,同时也开始发出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淫叫声∶「哦┅┅好舒服┅┅快┅┅用力┅┅哥┅┅用力┅┅妹妹要┅┅」 她的淫叫不同於老婆阿美的大呼小叫,而是细细柔柔的,但仍然带有急切的味道,让人感觉到她的快感正在急速增加中,已经快到高潮了。 果然,她在叫了一阵子之後,声音渐渐转弱,动作也慢了下来,最後竟然完全停止,屁股用力往下一坐,让我的老二紧紧顶住她的穴顶,接着,我感到一股淫液从她的子宫口喷出,她「呀」地叫了一声,然後身子往前一倾,整个趴在我胸前,并且紧紧抱着我。 我知道,她来了。而我这时也濒临爆发边缘,於是我也抱着她,翻转身,把她压在下面,发挥出最後的爆发力,又凶又猛地连续抽插了几十下。然後,我也泄了。 我们两人喘着气,身体叠在一起,躺在浴室地砖上休息了一会儿,再起来冲洗乾净。 洗完澡,我和小莉来到他们夫妇的主卧室,双双躺在床上。 躺在软软的床上,搂着小莉香喷喷、软绵绵的胴体,虽然从进门到现在已经连续大战两次,但我的小弟很快又硬了起来。 「哦,你又硬了呢,好厉害喔!」小莉马上感觉到了,她伸手握住它,把玩着,脸红红的,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在她的玉手把玩下,我的老二越来越硬,红通通的,昂然挺立,像极一尾就要发动攻击的毒蛇。小莉玩着、玩着,终於忍不住张口将它含住。 阴茎被含在小莉温热的口中,让我舒服得忍不住发出「喔」的一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小莉在含了我的老二後,竟然开始套弄起来,而且她的含功居然很棒,小嘴上上下下很有规律地套动着,传来阵阵刺激感。 更妙的是,小莉的屁股这时正在我的脸前。随着她嘴部的套弄动作,她那圆润的两片屁股肉就在我眼前上上下下。我先是抚摸她的屁股,接着,轻轻拨开她的两片屁股,让她的小穴清楚呈现出来。 一如其人,小莉的小穴也长得很秀气美观,浓密适当的阴毛长得很整齐,粉红色的穴沟微微张开,露出里面鲜美的穴肉,阴核小巧有如樱桃。看着,看着,我忍不住伸出舌头,开始品起玉来。我先是舔舔她的穴沟,接着伸长舌头,向着她的穴内舔去,尤其是那粒阴核,我更是一下接一下舔个不停。 这下子可让小莉刺激得快受不了。她加快了口中套弄的速度,并且发出模糊的呻吟声∶「嗯┅┅嗯┅┅哦┅┅哦┅┅」 我们如此相互口交了十几分钟,两人兴奋得快接近疯狂。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推开小莉的屁股,把她翻转过来,我坐直身体,再将她压在下面,提起被她含得坚硬如铁的大鸡巴,猛地往她的小穴一插,「滋」的一声,大鸡巴全根尽没。 毫不迟疑地,我开始不客气地狂插猛抽地来,小莉也卖力地逢迎接送,口中发出淫叫声∶「哦┅┅哦┅┅你好用力┅┅干得我好舒服┅┅哦┅┅对┅┅用力┅┅用力┅┅」 我一鼓作气猛干了十几分钟,开始觉得有点累了,於是动作慢下来。正被我干得性趣高昂的小莉显然马上觉得不过瘾,她推开我,翻身而上,坐到我身上,抓住我的老二,对准她的小穴,坐了下去,然後疯狂动作起来,先是上上下下起落,然後前後摇动,接着,她的浑圆屁股竟然转起圈来。 想不到外表文静端庄的小莉,竟是如此高明的性爱高手,她这一连串动作,让我的大鸡巴在她的小穴内得以尽情上下左右抽插,不但让我觉得雄风万丈,神勇异常,大鸡巴也因而碰触到她穴内的各个角落,让她的快感达到最高潮,但见她在我上面全身摇晃,头部摆动,秀发飞扬,一对豪乳上下左右晃动,构成一幅狂野动人的画面。 小莉这样子骑了约十几分钟,突然大叫一声∶「哦!」然後整个人趴在我胸前。我感觉到她的穴顶有一股热流喷出,浇在我老二龟头上,她的穴肉也一阵紧缩,把我的鸡巴夹得紧紧的。我知道,她的高潮来了。 而我也差不多了,於是,我紧紧搂着她,来个大翻转,将她压在下面。 我半跪在床上,抬起她的屁股,把握爆发前的最後一股力气,尽情抽插,我有时是把她的屁股往我这方向拉过来,有时候则是把我的屁股往前顶,前迎後顶,干得舒服极了。 而大泄後的小莉,在我这最後一波猛干下,可说被我干瘫了。但见她脸色苍白,气息微弱,只能紧紧抱着我,随便我干了。 终於,我觉得要来了。我放开小莉的屁股,把她紧紧压在床上,使尽全力,再向她穴内猛插了两下,然後把我的鸡巴紧紧顶住小莉穴内最深处。 我的鸡巴涨到最大,然後跳动了一下,一股浓浓的精液随即快速喷出。 小莉两手紧抱着我的屁股,让我的鸡巴和她穴顶做最紧密的接触。 这场今晚最激烈的做爱结束後,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喘息不已┅┅回到家,当我走进大门时,一名年轻男子正好从电梯中走了出来,和我迎面擦肩而过。我觉得那人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进了家门,看到老婆的鞋子整齐地摆在鞋柜前,看来她已经回来了。 我直接来到卧室,老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睡着了。房里只开着床头的小灯,灯光很暗。浪漫的昏黄灯光照在老婆美丽的脸上,显得那麽诱人,让我看呆了。 我真不应该,竟然放着老婆在家里,在外面搞到这麽晚才回家。我愧疚地弯下腰,亲亲吻了一下老婆的嘴唇。 老婆张开眼来,发现是我,很高兴地说∶「哦,老公,你回来了。」她伸开两手,搂着我的脖子,献上甜美的一吻。但她身子这麽一动,原来盖在她身上的薄被马上滑落,露出她裸露的上半身,两粒饱满的丰乳傲然挺立。 我觉得有点奇怪,一面吻着老婆,一面伸出一手拉开盖在老婆身上的其馀被子,一具完美无瑕的美丽胴体呈现在我面前来。老婆竟然是全身赤裸的。我再看个仔细,发现老婆满脸通红,春意盎然,秀发乱。她的衣服全散落在卧室地板上,床单上则有一些水水的痕迹。 我脑中轰然一响,推开老婆,很生气地质问说∶「老婆,这是麽回事?」老婆不但不害怕,反而竟然笑嘻嘻地问我∶「你刚回来吗?难道没在楼下碰到什麽人?」 我这时突然想了起来,刚刚在门口与我擦肩而过、让我觉得有点熟的是谁。 他是小莉的先生°°小高。 「老婆,是小莉的先生,小高���?你┅┅你┅┅你跟他怎麽了?」我厉声质问。 我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一把拉开老婆的双腿,让她的小穴显现出来。我赫然发现,老婆的小穴略微有点红肿,穴肉有点往外翻,露出一些红红的穴肉。 我更发现,老婆的小穴口滑滑黏黏的。 我伸出一根手指往她穴口一抠,抠出一些黏液来。我把手指拿到鼻前一闻,有点熟悉,又带点腥味。我内心里大叫一声「不好了」,那肯定是老婆的淫水和某个男人精液的混合体。从这些情况来判断,老婆肯定和小高干上了,而且老婆显然被干得很惨,因为连小穴都被干得外翻。 看看老婆满脸春意和玉体横陈的模样,再加上床上被单零乱,污痕处处,不难想见,刚才老婆和小高在我们床上这块战场的「战况」有多惨烈。 「老婆,你┅┅」我指着老婆,气得说不出话来。 老婆还是一点也不害怕,她笑着反问说∶「你呢?怎麽到现在才回来? 小莉很不错吧?够骚够辣吧?你跟她一定干得很爽吧?干了几次呀?从实招来!」 听到老婆这样追问,我心中突然明白过来,怒意顿消,反而觉得有点乐。 「嘻,老婆,没有什麽啦,我只不过跟她干了三次而已┅┅老婆,这究竟是怎麽回事呀?」 老婆以撒娇的声音说∶「人家是发现你对小莉很有兴趣,所以才恳求她和你上床,求了半天,她都不答应,人家只好牺牲自己,说愿意和她先生上床做为交换条件,她才答应。」 听她这麽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但也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但一想到小莉的床上表现,我心里还是很乐,觉得这样的交换真的很不错。 老婆大概看出了我内心的感觉,她笑得更开心了∶「看看你,大色狼一个,干别人的老婆,还干得那麽高兴。」 我不知道该说什麽,只好傻笑着。 老婆得理不饶人,竟然对我娇嗔起来∶「都是你啦,为了让你干小莉,害我被小高干得好惨,你看┅┅」老婆说着,用手扒开她的小穴让我看∶「你看,我的穴穴都被干红肿了,你摸摸看嘛┅┅」 看到老婆的娇娆模样,我不禁又兴奋起来,於是马上以最快速度脱光衣服,露出又再度昂然挺立的大鸡巴,很快上床朴在老婆胴体上。 我说∶「好的,老婆,我就用我的大鸡巴摸你的小穴吧!」说着,我下面一挺,大鸡巴就插进老婆的小穴。由於老婆的小穴还留有淫水和小高的精液,润滑度很够,所以大鸡巴很顺利就插了进去。 大鸡巴一插进去,我就觉得好爽,因为老婆的小穴这时有点红肿,所以造成她穴内的空间缩小,把我的鸡巴夹得更紧,而且由於穴内滑顺,抽插起来更觉顺畅。於是,我不客气地猛烈抽插起来。 「哎哟,哥哥,你好狠心,人家穴穴都肿了,你还要插人家┅┅哎哟,很痛呢┅┅坏哥哥┅┅你要插死妹妹了┅┅」 老婆嘴里虽然喊痛,但屁股却拼命往上顶,尽情迎接我的抽插,脸上陶醉的表情也透露出,她其实是很乐的。 果然,在我猛力抽插了大约一百下後,老婆就乐得发出她惯有的淫声浪语,而且声音极大,惊天动地的∶「哦┅┅哦┅┅哥┅┅用力插┅┅用力┅┅哦┅┅顶到穴穴头了┅┅哥┅┅好哥哥┅┅用力插妹妹┅┅用力┅┅」受到老婆如此夸奖和鼓励,我当然插得更用力,每一下都全根尽没,一直插到老婆小穴的最深处。 我一面插,一面气喘吁吁地说∶「老婆┅┅我插得好舒服┅┅你的小穴肿肿的,反而把我的鸡巴夹得更紧┅┅对了,你小穴内为什麽那麽滑顺?是不是小高的精液起了润滑作用?」 老婆羞红了脸∶「讨厌┅┅都是你啦┅┅一进门就要插妹妹┅┅人家还来不及去洗乾净┅┅你就插进来了┅┅哦┅┅」 听老婆这麽一说,我脑中不禁浮现出老婆和小高作爱的情景∶小高个子高高瘦瘦的,模样精壮,性能力应该也不错,看老婆的小穴都被他插红肿了,就可以知道。 想到这儿,更增添我的性趣,令我更加兴奋。我一面插,一面大叫∶「插死你这个骚货┅┅插死你这个喜欢被人干的骚货┅┅」 【完】
17 notes
·
View notes
Text
【透哀】七哀
降谷零×宫野志保
首发ao3
一
志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母。相反,她对子女的管束教育非常严格。严格到了那信奉“放养教育”的侦探每次看到她都要戏谑两句“母老虎”“太不人道了”之类的怪话的程度。
曾经某次那人问她“当时也没有见过你有这么严厉的一面啊。对当时我们身边那几个调皮的孩子你不是一直都很宠他们的吗?”
“他们是我的孩子吗?”她反问。
她的家并不算大,但是总是一尘不染。虽然研究所的工作很忙,她依然每天要和孩子们一起把屋子打扫一遍。反过来看看那个宛如垃圾制造者一般的,总是要靠做家庭主妇的妻子打扫才勉强让住的房子有个人居所样子的侦探,她实在是想不出为什么他总是要去戏谑她。
地面瓷砖亮得能照出她的茶发,窗户就不必说了,咂舌的是纱窗也能洗得显出原本铁纱的颜色——而大部分家庭的纱窗都很少清洗,掸一掸甚至能看到从纱窗的缝隙里荡出的,灰尘泛起的烟雾;橱柜里的碗码的整整齐齐;至于菜刀和锅,也因为长期清洗养护得法而显得出铁器特有的光泽。
做完这一切,孩子们央求着她要打开电视玩游戏。在娱乐方面,她倒是很少干涉。志保没有那种所谓“东亚中产阶级的幼稚病”——即总是想把自己出众的替人打工的技术移植到自己孩子身上。孩子们很聪明,最大的现在也不过才上小学三年级。志保厌恶提前教育,所以从不主动让孩子们去任何补习塾。
她虽然知道这和她小时候的情况完全不同,但她却还是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失去童年。而至于严厉的一面,则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和生活技能教育上。
孩子看着母亲似乎没在听着他们的央求,心中不免沮丧。正当他们想着是不是应该跟母亲提出想要做点什么劳动来换取游戏时间的时候,却听到了那期盼已久宛如“仙音”的赞美。
“可以,注意时间。妈妈先给你们做饭,一会儿记得吃。”
“那妈妈你呢?你不在家里吃吗?”她的限外之意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就被他们点破
“妈妈晚上出去一会儿,你们到点了就按时睡觉,不要让妈妈担心。”
“谢谢妈妈!”这句话孩子们是背对着她的脸说的。在她还没说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奔向游戏机了。至于有没有听到她的后半句,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微笑扶额,她完全可以理解。当时元太步美光彦几个孩子,不也是看到游戏就这样子走不动嘛。小孩子天性爱玩,她反而高兴。
她晚上做的是意大利面。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倒是她在偷懒。曾经,也就是大概十年前吧,她在给阿笠博士做饭的时候可总是绞尽脑汁研究菜谱,想着怎么把低卡和营养结合在一起。不过那时的她终究只是个小学生,没什么事也不大用照顾人,自然可以把相对来说更多的精力放在这种生活琐事上。
走出电梯,她其实也没有想好去哪。她爱她的孩子,不想让他们再像自己当年一样身边举目无亲,精神上简直每天都要面临阿尔志跋绥夫式的绝境。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与小孩子相处这件事本身多么令他享受。尤其是这是她独立带孩子的第七个年头。
她也需要一些私人空间。
仲秋时节,晚间的天气已经有了些许凉意。太阳还没有彻底沉向西方,昏黄的天光与四周的黄叶似乎融为了一体。风止住了。不知不觉中,日光已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但那影子却也因越来越昏的光照而显得面目模糊。地面被着枯��,黄澄澄的,叫人好生困乏。她眼前也多了几分恍惚。
研究所的工作强度很大。之前组织统一体检的时候她被查出有贫血的症状。她也不再是以前那么个无牵无挂的愣头青,倒是很老实地遵从了医嘱。随着在研究所地位的稳固,她也慢慢开始把一些项目分派给同僚——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有机会在现在还能在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
毕竟,她不能不负责任。
邻国的传说讲这个时候的月亮是一年之中最圆最亮的。她虽然喜爱读书但并不痴迷文学,也就没有那些所谓文人赏月咏月的情致。
推开熟悉的酒吧的门,昏昏欲睡的侍者看到熟悉的身影并没多搭话。只是一如既往地倒了两杯酒放在了她最习惯做的位置前。
Bourbon和Sherry。
她不愿意去回忆那些过去。Sherry的日子是不堪回首的回忆,她一点都不想再让自己和那灰黑但是却有着甜腻迷醉感的生活再搭上关系。她选择这里也大致只是因为冷清无人,萧条的感觉配上昏黄的灯光特别适合遮盖她的脸。
“来了?”身兼数职的店主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某天晚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到访的女子。事实上他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在某些令人愉悦的时候——比如店里罕见的出现了十多位酒客——面前的女士在门口稍作徘徊最后竟然原路返回。
打听顾客的隐私是不好的行为。除了她们喝到半醉,理智再也管不住嘴巴之后开始冗长而又琐碎的倾诉的情况下。
宫野志保想起自己与面前这个叫“礼”的男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离开的第一年。当时她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而第一个孩子也才刚刚两岁。作为实质上的单亲母亲,她那一年的生活无疑艰难——其实也还好。最寂寞煎熬的日子她早就尝过,也体验过隐姓埋名和终日提心吊胆的第二次童年。不过刚刚到来的一丝幸福被再一次的夺走,得而复失总是最让人难以接受。
她终于过上了她向往已久的平静生活,可是,在偶尔从看见东京塔的掠影时,还是会发愣地想起,那些属于灰原哀的日子。
看来人总是这样,贪心不足蛇吞象。她怀念的其实不是灰原哀。而只是突然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还有这所谓“亲人”存在的那一刻惊喜与酸涩,只是另一个男人身上淡淡的咖啡与甜点香气和温暖怀抱。
只是,那段岁月在两人双双回归原位之后突然间变成了爱情,而又突然转折向了另一个不知道该如何言讲的境遇。爱情这种东西,即使再刻骨铭心,但如果某一瞬间,连结的纽带——空间与时间割开,他们就变成了断桥两端的人,隔着滔滔不绝的如斯逝水,背道殊途。
二
点起一根烟,她并没有急着动面前的酒。只是在店内剩余两人见怪不怪目光的注视下把Bourbon和Sherry混在了一起。两种近似蜂蜜色的酒发生碰撞,很快就融合成了一杯看起来就很可怕的液体。
“你还是总这样喝。我建议你自己买。这样糟蹋东西的话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礼扶额,有些无奈的看着这个女人。
“不想给家里的孩子留下一个酗酒母亲的印象。毕竟再怎么样也是要考虑家庭教育的因素。”她只是抽烟。烟气漂浮起来,在光的照射下产生了丁达尔效应。她的面孔更加模糊,模糊到了礼似��也记不起她五官的程度。
“怎么?说辞又变了?我印象里你上一次的借口是工作太忙,上上一次的借口是……”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吗?”说出的话并不友善,可她语气倒是很平静。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安室透离开,或者说不告而别的七年里。她在表面上并没有展露出丝毫不同。唯一一次失态,可能是她阿笠博士离世后的那天晚上。她罕见的来这里说了很多话。包括不告而别的男人“零”、骤然离去的长辈阿笠博士、自己家里讨人厌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总是把她逼到矛盾死角的两个孩子……
她在喝醉的时候也很克制。没有说出有关灰原哀、有关宫野明美、有关赤井秀一、有关江户川柯南、有关GIN、有关……她确实看起来很像最近几年兴起的那种“既是职业女性又是家庭主妇”的顽强单亲妈妈。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某种喜欢絮絮叨叨的大妈心。
不过对于宫野志保本人而言。虽然恐怖和温暖并存的记忆可以慢慢模糊,和安室透相处时的习惯却顽固地生存了下来。这两年,她依然时常熬个夜,顺便也学会了他拿手的三明治和各种甜点。孩子们以为妈妈有着好像超人一般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出全米花最好吃的饭菜,可是她知道这只是在追寻他们父亲的味道而已。
除了看上去很可怕的戒断反应,让她在咖啡这件事上举棋不定。其他的,在那一次意外的醉酒之后,宫野志保自认为快刀斩乱麻,过得非常高水平。
一切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妥。
她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狂热的喜欢比护选手——不过还是有赛必看。听的歌也从流行到jazz到金属再到R&B再到古典最后转回到了摇滚乐。最近似乎是看了不少假面超人之类的东西。GIN已经死了,组织也灭亡了。看着两个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东西抱着她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去家长联谊会的时候难道她还能狠心拒绝吗?为了不丢脸,她很是恶补了一些现在小朋友们喜欢的东西,却惊愕地发现和她做小孩时候也没什么不同——还是什么戈梅拉、假面超人之类的玩意儿。
那一次家长联谊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似乎成功到影响了不少小朋友的家庭关系——参加活动的男家长被她的魅力倾倒、参加活动的女家长被她的衣品倾倒。似乎还闹出了什么离婚风波之类的搞笑事情。不过在这之后,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地位似乎是有了显著的提高。
回忆的时光总是极快。她抬了抬头,看见今晚的月亮果然极亮。如同一颗白色莲子一般挂在天的那头。圆如铜钱,白似冰屑,中间微微颜色深浅,四周白蒙蒙地发出一团光晕,恰似灯影透亮。
这一段时间过得实在艰难,一个人不想说话,另一个人懒得说话。压抑之下,最终还是礼先开口了。
“是不是有些怨恨,对于您先生?”
“你听说过一首诗吗?叫《七哀》。”志保反问。没有什么情绪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只点一杯Bourbon和一杯Sherry是她的原则。第二天还要准备早餐、送孩子们去学校、再到研究所打卡上班,她不能喝太多。
“我又不是文学爱好者,你问错人了吧。啊,欢迎光临!”礼说着,并没有起身去迎接新来的客人。只是从下面装瓜子的盘子里摸出一颗放在两指之间。用力一弹,瓜子径直飞向昏昏欲睡的侍者。侍者猛遭重击,一个激灵爬起来看向礼。他给侍者使了个颜色,这才看那懒汉拿着酒水单走向新来的那个女客。
“没听说过就算了。一份三明治。光顾着给孩子们做饭了。”她的脸色有些怪异。
“又犯胃病了,我也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不要空腹喝酒。”礼说话很小声,至于志保有没有听到,他完全不知道。不过做三明治这种事情他自然是轻车熟路。切掉面包的四个边,放在小小的电蒸锅里蒸一下,把蔬菜和肉类切片,加入掺了味噌的酱料……
“啊,老板。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多少钱。”隔壁女客指着礼手里的三明治道。
“啊对不起小姐,这位是我们这里的熟客,这些材料都是她寄存在我这里的,所以……”礼没说完,就被志保打断。
“也给她做一个吧。毕竟这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她说,“虽然你的三明治水平总是会有着奇怪的波动。咖啡也是。”
礼的瞳孔骤然收缩。幸亏灯光昏暗,大概是看不清他脸上一瞬间的变色。他也不想聊文学。这一瞬间那位女客的打岔反而是救了他一次。
三
其实,安室透和宫野志保的婚礼并没有任何人参加,甚至连法律上的效力都不具有。他们也只是告知了最值得信任的几个人:比如工藤新一,比如阿笠博士,比如服部平次。这个消息甚至连小兰都不知道。
毕竟她并不认识“宫野志保”,只知道那个在工藤新一回来后就去英国和爸爸妈妈团聚了的“灰原哀”。当然,之后她还是以“工藤新一查案期间的法医搭档”的身份去见了毛利兰。她和毛利兰之间的交往并无任何生分,毛利兰说他们“一见如故”,但她不知道,其实宫野志保心里是拿她当亲姐姐看的。
婚礼极小范围内举行,这是志保的主意。她其实还是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心结。她还是讨厌热闹,那种寒暄令那时的她无所适从,甚至会想到组织里的虚与委蛇。
至于没有填结婚登记表这件事,是安室透的主意。毕竟,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叫“安室透”,有的只是“降谷零”。他作为“零”的负责人,是不可能舍去“安室透”这一身份而以真实的“降谷零”身份活动的。也是这样,宫野志保也没有改姓安室或是降谷或是某个降谷零的其他假身份。
毕竟这世界上的危险犯罪组织可不止有酒厂一个。
不过虽然是这样,最开始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那时候安室透不怎么上班。依旧是老样子的每天到处打打工做做侦探。一天里有大把的空余时间逗哈罗和志保。而志保则是在忙着找工作。
晚上他们一起看电视,听音乐。躺在床上听Cinderella。一团浓郁的悲慨。志保没再说话,闭起眼睛。床太软,在被刻意调低了的音乐声里,她发现自己在悬浮。悬浮,时起时落,失重。
零其实也很惊讶。他才发现原来她这么高,之前他们两个最初开始相处的时候她还是小孩子,总是穿着软底的儿童鞋。如今她和他抱在一起,他才发现宫野志保也只仅仅矮了他一个头。
她的肤色更苍白了,再靠近一点,他估计能看清脖子上青色血管的脉络。是因为她长期在地下室工作、熬夜和贫血的缘故吗?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事实上安室透最开始对她流露出善意是在他确定了她是艾莲娜老师的女儿之后。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从未看到她真正的样子。虽然当时的熟人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叫他们安室先生和小哀,但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举目无亲。两个假身份的人生没有证据,是个既无过去,亦无将来的特殊存在。想要永远保持着这一把指间沙,他抓得越紧,就流得越快。零从事的是最危险的职业。他承认他自私。他不想在将来的某一日,他躺在一片血泊里时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漫长的梦境。
直到带着咖啡气味的呼吸迫近。志保感觉到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胸口上轻轻地抚摸着。这不对。她虽然已经这样的年龄,虽然和那个男人已经结为了二人都认同却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夫妻,虽然对于降谷零这样的男人她一点都不介意投怀送抱,但显然,她还是有着一般女性在此刻的生涩。此刻她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也没有提前预备好防护措施。
情欲来得莫名其妙。空气里有种危险的甜腻气息。她的身体确实很敏感,不一会就开始浑身抽搐。她想推开降谷零的手,但她又怎么能和降谷零抗衡?更何况她其实在心里并不抵触,只是好像暑假里犯拖延症的学生——总是觉得今天还没有到写作业的时候。
降谷零又抱过来。这不对,宫野志保的手只是见招拆招,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思考。降谷零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对视。她似乎一瞬间就被抽走了魂魄。她想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时他穿着黑色的大衣,身姿颀长,小麦色的皮肤似乎被寒气冻得有些苍白。
他不说话,只嘴角带了不知道是何意味的笑,垂着眼看着躲在博士的身后心惊胆战的她,瞳孔里闪闪烁烁,恍若星河。
和今天一样。
他的指尖冰凉,顺着袖子滑到她的T恤底下。她退到了床沿边,却被他伸手捞了回来,顺便解开了内衣的扣子。志保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惊慌地转过脸,却一时间不知道中了什么魔,在他留长了的金发下面找到了他的嘴唇,报复般地狠狠亲上去。
那之后,她扎进降谷零怀里,在他胸口靠着,无端想哭又没有眼泪。她曾经暗戳戳地恨过父母。为什么要生下她,就是为了性爱时一瞬的快感吗?如果是这样也太自私了,她宁愿一辈子也不要做这种事。不过她终究还是沦陷了,甚至想……
再来一次。
她又往降谷零的那边挤了挤,给出一个眼神作为示意,之后马上从被子里钻出,只是鸵鸟式地把头埋进了洁白的被子里。降谷零一愣,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拍拍他的后背,拉过被子来把她再一次的吃掉。
那一次之后,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顺便一提,姓宫野。
四
宫野志保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时不时那一块乏人问津的狗皮膏药。现在她非常理解当时毛利兰的感受。
她在之后去过工藤新一家几次,却发现似乎她眼里的理想情侣也过得不是那么幸福。她比毛利兰更懂得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在做很重要的事,却总有一个自己割舍不掉的人用眼泪扰乱自己情绪”的感觉。这种时候,两人之间再深厚的感情也会变成毒瘤。他们无法联络,更谈不上见面。工藤新一侦探在全日本满山海跑着缉凶,反而是留下毛利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东京操持一切。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他们和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沟通彼此之间的问题,而他们在各自的城市还要独自面对一切的不如意。毛利兰很坚强,或许是源自于工藤新一在幼儿园时候不经意间下的一句“爱哭鬼”论断的逆反心理。不过就算是这样,她还是难以接受工藤新一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不耐。
那天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来见宫野志保。
“安室先生……还没有回来吗?”她看着宫野志保家里的凄清冷寂和两张婴儿床,一肚子的牢骚和委屈瞬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应该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毛利兰分明地感觉到自己的心骤停了一下,像是非常艰难,她看着若无其事的宫野志保试探地开口:“可是,安室先生不是……怎么会?”她咬着嘴唇,似乎是把自己代入她的悲伤角色去了。
宫野志保没有隐瞒,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其实现在再瞒天瞒地并没有什么意义。她在这时会来找自己已经证明了这种绝对信任。而黑衣组织也已经被连根拔起死的不能再死。现在继续的隐瞒,除了加剧面前这位女士和他丈夫的不信任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她去开了两瓶酒,是GIN和VODKA,他们的故事也就从那时开始。
边喝边聊,出乎意料的是兰对事情惊人的直觉。在志保说到很多她都感觉离奇的事情的时候,毛利兰的眼神里只有释然而没有惊愕。
“看来,你早就猜出来了吧。只是理智上不愿相信。”酒精让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再使用敬语,随便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他们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
顺便一提,那一天是十二月三十日,工藤新一依旧在山梨的山沟里查着一桩牵扯了十四条人命的连续杀人案;而降谷零也依然渺无音讯,所知道的只有风间在降谷零离去后的第三天送来的,黑田兵卫签名的调查文件的影印件和一句“去执行秘密任务,可能需要很久。抱歉降谷夫人。”的口信。
“要不然,出去吃点什么?”毛利兰发出邀请。她似乎稍微快乐了一点。也不知道她突然想通了什么。
某种程度上宫野志保承认自己很物质。她穿的那件黑色大衣是C家出的鹤纹刺绣复古款,价值不菲。手提包、鞋子和帽子更不必说。这些衣服基本都是她还是“灰原哀”的时候他买给她的。
他说:“组织的经费,不花白不花。”
事实上她完全理解。对于组织——或者说是公安之类的人。所谓存款,大部分都是可笑的数字而已。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存款可能存着存着就不是自己的了。所以,那些人的生活一般都极度奢靡,就连宫野志保也不能免俗。喜欢名牌的毛病,大概也就是那时染上的。
毛利兰偷偷打量着宫野志保的长相。宫野志保其实算不上标准的美人,在欧洲人眼里,她的五官太清冷,并没有欧美人喜欢的那种“魅惑”“性感”、更没有欧洲人眼里典型的东方美人——比如章子怡——那样复古的五官。这是因为她的日英混血,多少柔和了东方人的特质。没有西方人风情洋溢,却比同龄的西方人显得年轻素净。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时代发展。不少时尚圈的所谓“艺术家”开始推崇高挑瘦削、冷漠苍白的偏禁欲主义。时尚杂志上很多模特的长相都是她这一款,不少国际大牌也专门为着这些模特设计了适合这种长相穿戴的服饰。再加上她出众的如高岭之花一般的气质,反而给她增添了十几分的美。
不过可惜的是,这样两位美女竟然很不顾形象的在一个苍蝇馆子里撸着串。那年的雪来的好晚。十二月底才开始洋洋洒洒的下这一年中的第一场雪。路灯的光被成片的银白色衬得金黄,半弯冷寂的弦月尚还挂在天边,茫然吹起了风。
毛利兰递给她一支烟,问:
“一个人的时候会抽一支,尤其是……”
“在跟工藤吵架之后?”她接过来。其实她不会抽烟,不过还是有样学样地点燃,浅浅地吸了一口。舌尖有些麻木,在烟气通过喉咙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预料之中的辛辣和刺激。
毛利兰不置可否。她其实早就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当时的几个朋友没有修成正果的。园子忙于铃木集团的事务,京极真依然是全世界的参加比赛。双方都有自己忙碌的事,偶尔见一面反倒是甜蜜得紧。至于服部平次和远山和叶,似乎双方都在保持着一种刻意的距离——虽然早已是男女朋友多年,但谁也没有提出结婚的事情。
在来找宫野志保之前,她先去问了远山和叶。得出的答案却是让人大吃一惊。
“我和平次就是有点互相喜欢,这么多也习惯了老玩在一起罢了。不过兰酱你也知道,我们经常吵,我也对推理没什么兴趣……就是说,虽然已经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互相都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羁绊住对方,除非我们之间谁做出天大让步。”电话那头的声音虽然还是有着浓重的关西口音,但终究已经没有了那种过去的天真烂漫在里面,“所以,其实兰酱你还是要看开一些。工藤君他终究还是爱你的嘛,这点你应该最清楚了啊。”
她语塞,垂下眼帘,最终一言不发。
“志保,你说,我是不是天真的有些过头?”她问,“你难道就不难过吗,安室先生……”
顺便一提,毛利兰大学念的是早稻田的文学。一个很多女生都会选择的专业。在日本这样的社会里,女性选择文学就好像古代皇帝身边总要有几个舞文弄墨的馆阁文学者一般,只是贵人或是她们丈夫乏味生活里的调剂品。毕竟,比起出门打拼,还是有更多传统的日本男性中意于温婉柔和,善解人意的“大和抚子”。如果能再有点“红袖添香”的情调,就更完美了。
所以毛利兰会觉得艰难也是正常。长期浸泡在太宰治、川端康成之类的日本文学里,总是会有那种“情绪急转直下”的时候。悲观是一种底色,而敏感则是这种底色伸出的触手,用来折磨自己。
“我难过又能怎么样呢,兰……桑。”她仔细考虑,还是用了这个略微正式却又不嫌疏远的叫法,“他有他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我这个人就是一忙起来就会忘记很多事。”她想用酒堵住嘴,拿起一根烤得冒油的鸡肉串吃了一口,又马上灌了一口酒。
“不坦诚。”她还是那么敏锐。
“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啦,只是……”她刚想说,却被毛利兰打断。她从包里摸出一个本子,掏出钢笔,在上面好像写着一些什么。
“喏,给你看。”写完她把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递给志保。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三国魏·曹植《七哀诗》
五
“想什么呢?”礼点了点她的胳膊,“不会就这一点就喝醉了吧?”
看了看钟表上的时间,她才发现正如礼所说。她居然已经发了大概四五十分钟的呆。
“一样再来两杯。”她说。
“怎么了?喝这么多?”作为酒吧老板的立场这样说本来就很奇怪。生意已经很差了,看到这样的酒客即使不说劝她多喝两杯也不应该无意义地在这里像八婆一样问东问西。
她没回话,其实她并不是很喜欢和别人进行长时间的无意义交谈。安室透离去的第七个年头的确很让人痛苦。当年她读死屋手记,写戈梁奇科夫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如同“死屋”。她虽然环境不如那般恶劣,但终归不是好感觉。所以她痛苦。不过如果是GIN的话一定会骂她安逸的太久,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朵“坚韧的玫瑰”了。
说起来GIN的确很喜欢这样的修辞。带着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奇怪的语言风格。如果抛开他做的那些勾当,其实这个人的性格反而像一只喜欢虚张声势的刺猬——表面上看起来冷酷,但是操纵他所有行为的逻辑却好像是一个和容易别人闹别扭的倔小孩儿:肆意妄为、不听劝阻、说干就干、认准的事情就绝不回头、从不考虑后果。
她在作为“宫野志保”时的少年时代没什么好回忆的。她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纯粹学习动力,纯粹是因为她觉得学习很有趣。
尤其是在时时刻刻都有组织成员监视的情况下。
娱乐只有电子游戏,她不爱打游戏。社交么,她一个亚裔女生,还只有十五六岁的年龄。自然是被所有人孤立的对象。
学习才是他唯一和正常人世界的沟通桥梁。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做项目的时候,她才能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学生。
没人愿意和她进行小组合作,她就自己一个人包揽所有研究工作。因为她觉得那很快乐。
化学对她来说,是阳光,是姐姐,是几乎没有见过的爸爸妈妈。
另一方面,当时,和她一起在美国受训,也是主要负责监视她的组织成员是GIN。
那时她就厌恶这个男人。生理性的厌恶。但GIN却做的尽职尽责。除了自己的训练,他几乎一步不离开她。
但他从来不在她被欺负时伸出援手。反而他骂她。
“不争气,没出息。”伴随着的就是一顿毒打。
所以后来她半开玩笑的对降谷零说自己三脚猫的格斗术是被GIN打出来的。
现在,她已经可以用云淡风轻的心情看待这样的事。但当时不行。
琴酒对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甚至是生理期和内衣尺寸。对于在美国接受能力训练的他来说,通过垃圾袋和表情饮食之类的要素观察出这些几乎是轻而易举的。
“志保,其实GIN喜欢你在组织高层里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不过几乎所有人都瞒着你。”某次做完,降谷零曾经对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讲笑话?他比我大了十几岁。”宫野志保不是情感白痴。她完全可以体会到GIN对她的那种变态式的情感。不论是后来想想仍然心有余悸的“头发丝认人”“听喘气认人”,还是最后决战时他打她的那三枪。
决战的具体经过她已经记不太清。只是在甚至连BOSS也已经落网的情况下,唯一还在抵抗的人,也是GIN。
后来在某次看比护选手球赛的时候他才体会到那种感情。那是一场保级战,在东京出名,在大阪走向巅峰,后来在英格兰大杀四方的比护在濒临退役的年龄落叶归根回到大阪。不过此时的球队已经今非昔比,从冠军争夺者混成了保级队。
那是最后一场的生死战,赢了就保级,输了就降入J2。
比护首发,也成功完成了帽子戏法。可惜球队的后防如同组织一般出了亿个卧底。最后一次的射门机会,他拼了老命的倒地铲射,把球捅进了球网。比分被追成了4-4,他也因为没有躲开对面���守队员凶狠的铲断而导致胫骨直接骨折。这样的重伤直接给已经38岁的比护隆佑的运动生涯判了死刑。而令人悲伤的是,虽然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球队还是因为胜负关系的缘故降到了J2。
那之后她罕见地主动打电话找毛利兰出来喝酒。工藤新一的东京灵魂又一次夺冠,喜不自胜的他打电话回来也在和他妻子聊这件事。听到志保讲这件事,她反而是给志保讲了一段三国的故事。
赵云随诸葛武侯出岐山时,看着自己身边关兴,张苞这些小子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心中会不会也有“老了”的感觉呢?
也正是那一刻她才明白当时GIN的感受。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退场。GIN就是GIN,不能接受像老鼠一样被人满世界通缉,追来赶去的苟活。就像诸葛亮必须死在北伐途中的五丈原、赵云在死前必须断后吓退曹魏士兵迸发最后一次的闪光一样。组织之于GIN,或者说是黑泽阵,就是一切。他从降生开始就注定了为组织服务,尽忠到死。那么眼看着承载自己全部生命意义的组织大厦倾覆,他会做出那种选择,完全符合他“虚张声势的刺猬型人格”的逻辑观念。
所以在她当时深入组织的研究所抢救最后的APTX-4869资料却和躲藏在那的GIN巧遇之时,GIN才会拿着枪,一步一步把她往门口逼。
那是个晴天,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志保站在门外可以被太阳光照到的地方,而GIN则站在了阴影里,面朝光。
他打了他三枪,左右臂各一枪,腿一枪。没有装消音器的枪声引来了公安和FBI,但在他们到来之前,GIN用最后一刻子弹结束了他自己。
当时的宫野志保百思不得其解,以GIN的能力,想杀死自己之后逃走简直是轻而易举。他为什么要自杀?
事实上,那三枪是GIN对自己的交代——他没有杀掉自己曾经唯一或许动过心的女人;也是对组织最后的忠诚——面对叛徒,他并没有无动于衷。
不过这种仁慈带来的矛盾也一直困扰着宫野志保直到降谷零走后七年的这个深夜。她对GIN并无任何好感,他夺走了她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甚至这种厌恶带有生理性质。
但也正是这个人,最后把她送出了困扰她近二十年的噩梦。这个噩梦的缔造者是乌丸莲耶而不是他GIN,而却是GIN在最后时刻用生命把噩梦引向了终结。
那她该如何自持?
六
时间大约已经到了十一点半。生意越发冷清。
“我在这里这么久,才喝了这么一点。你们是不是最讨厌这样的客人了?”她问,语气里有一点醉意。
“没什么,你还要喝么,算我请你。”礼说。
她还是没回话,只是自言自语:“礼,Rei;零,Rei。是巧合么?”
说起来,她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礼,又是什么时候和一个陌生男性以不符合自己一贯作风的情况下变得如此熟络呢?
“要杯茶吧,毕竟明天还要上班。就要……伯爵玫瑰吧。”
浅白绿色的花朵,带着馥郁的玫瑰香气,和她瞳孔的颜色一样,清冷又迷人。
突然,礼摸了摸她的手。志保皱了皱眉。冰凉的指尖碰到他温热的手掌,她冷不防顿了一下,却被礼顺势反手握住,整个手掌被团进他的掌心里,若有若无地被摩挲着:“手怎么这么凉……”
“你干嘛?非礼女科学家?”她挑了挑眉毛。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可是不管她怎样拔,都无法挣脱他。这样摩挲了一会儿,她的手和体温也渐渐暖了起来,感受到她手掌里细密的汗,礼松开手,轻松道:
“给你暖暖手。”
她瞪着他,准备张口反击,但想过后还是懒得和他争论。毕竟她和面前的男人熟络了之后经常吃他的免单。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她也实在是不好说些什么。
更何况,似乎刚刚她并不抵触面前的男人的亲昵举动。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她心里发苦“自己不会真的寂寞到想要有外遇了吧。之前和侦探处理了那么多外遇杀人的案子,难道有一天要轮到自己?”她越想越荒谬,竟然被这种荒唐的想法逗得笑出了声。
“今天就到这了,谢谢你的招待。”她站起身,头稍微有些晕。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喝了以往大概四倍量的酒。难道真是所谓的“寂寞”?
礼没有留人,只是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东京繁华,是个不夜城。不过这地方远离市中心的商业区,路上倒是没什么人。头顶路灯的光线一点点亮起,白色的光线在她背后晕开,她的头发被绕在耳后,耳廓边浮动着玉粉一般的浮尘。她弯起眼睛,略带得意地笑了。直到刚刚,她才想明白那种奇怪的熟悉感来自哪。就好像,整个城市夜晚的灯光都揉碎在她的眼睛里,连眼角的笑纹都带着绵绵缱绻的气息。
其实她本不应该如此欣喜。曾经她想过在她回来的时候她要怎样责备那个把他丢开跑了七年的人。但事实现在看来并非是像她以往想的那样。
找了个街边的长椅,她坐下。既然回来了,就让她也做一次“侦探”,梳理一下她和榎本礼的故事。就当做是给过去的七年点上句点。
事情的开端还是那一次兰的突然来访。她们两个那天晚上的最后一站就是那个灯光昏黄的酒吧。
听兰说,她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因为曾经她来这里抓小五郎回家的时候遇上了一起杀人案。后来事情不出意料的顺利解决,她也就和当时还是老板儿子的榎本礼有了一面之缘。后来她上了大学,和几个朋友来这里排过戏,也在这里陪失恋的同学喝过酒。似乎从那时起这个酒吧的生意就一直不佳。天知道小五郎是怎么找到这样隐蔽的地方的。
第一次见面,礼给她们端上的三明治居然久违的吃到了当时还在“波洛”打工的,降谷零独创的口味。当时礼说这些是给一位本来说要来但却临时改了主意的先生准备的。他们店里并不卖三明治。这样的做法也是一位厨师——那个曾经为了套出降谷零三明治配方而闹出很多笑话的厨师——专门教给他的。
她并没有指望着能在这里知道降谷零的近况。只是就当做怀旧也好,她还是爱上了这家半死不活的店。
她曾经问过他,在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稳赔不赚的生意。他只说这是他父亲所谓的“梦想”。宫野志保嗤笑,不过她也相信这种说辞。毕竟日本这样的国家,想找到什么奇葩应该也都是不难的。
后来无非是平淡日常。榎本礼的厨艺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做出超越当初降谷零的口味;坏的时候就只能模仿起味形而失其神髓。随着来这里次数的不断增加和榎本礼对志保身体状况的日渐担忧,这里几乎变成了她的食堂。哪怕是不喝酒,她也喜欢来这里坐坐,开着电脑写论文,吃一吃榎本礼时好时坏的饭菜。
其实有时候她想,正常的恋爱本就不该像她和降谷零一样牵扯到长辈恩怨、生离死别。刻骨铭心又畸形丑陋,进展神速又风雨飘摇。反而是应该在日常里慢慢累积。她自己都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可怕,但他们毕竟聚少离多。他们正式确立关系到现在是九年,在一起的日子不超过三十次。
越想头越疼。仲秋夜晚的风还是很凉。她每次出门穿衣都务求得体而奢侈。今日也是。本就白皙的腿被风吹着,白得有些吓人。都说饮酒之后会发热是因为血液循环加快,在风吹的情况下更容易丧失体温而得病。
她经常生病。不过她宁可撑着,即使撑不住也要让自己摸鱼的地点在研究所里的办公室内。日本的职场是炼狱,尤其是对于女性。她们大多要时刻保持强势,像是开了屏以虚张声势的孔雀。
“怎么不回家?”有人问。是降谷零的声音。而宫野志保并不惊讶。
“你先撕掉你的假脸再跟我说话。免得一会儿孩子们见到你以为我搞出了外遇。榎-本-礼!”
七
“志保,你早就看出来了吧。”他说,一边说一边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那张脸是属于降谷零的,货真价实的降谷零。
“不,今天,也就是刚刚才看出来的。不过如果你不说,这事也就永远成为秘密了不是?”她戏谑道。“那我们来解��解释吧,降谷先生。为什么你会在这?”
事情其实很简单。降谷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确实在参与调查一个跨国的贩毒和倒卖军火的团体。黑衣组织的事情之后,降谷零搞出了组织PTSD。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
他作为降谷零在“零”,也就是明面活动,同时利用“安室透”的假身份在暗中调查。至于那个小酒吧,从很早开始就是他们公安的一个秘密据点。至于那块钓上宫野志保的三明治,则自然是出自降谷零。毕竟,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安全得多。至于榎本礼和他父亲,自然是公安成员。后来,他在稍微空闲的时候会伪装成榎本礼和她见面。其实她本不该露出破绽。只是面对一脸无所谓,用最冷漠语气说出最惨淡现实的妻子,他总是无法克制。
“那我每次吃到好吃东西的时候,榎本礼每次几乎要越线的时候,都是你假扮的啰。”志保其实心里也暗暗释然。她其实也有对榎本礼心动过,但理智总是在一瞬间就战胜情感。虽然如此,也只是压制到普通朋友的程度,她完全无法割舍那家店带给她的,熟悉温暖又危险的气息。
“你这算不算逼迫自家妻子出轨?还有,结束了吗?”她问。
“结束了啊……风间和榎本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也可以从零组解放出来了。”
“也就是说?”
“是的,是你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
志保没说话,只是把她刚刚在酒吧里猜到事情真相的后写的一张纸条递给了降谷零。
“你看,这首《七哀》,男主人公是你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搂住了她的腰肢。降谷零贴过去亲吻他的侧颈。呼吸沉重,意图分明。
志保下意识地还觉得他是榎本礼,想挣开——毕竟那身衣服实在是太具有代表性了。可随着呼吸的临近和与榎本礼完全不同的声音,她也放弃了抵抗。
降谷零按着他的后颈对着他的嘴唇吻下去:“我可不是什么宕子啊混蛋!”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她叹了口气。
“不想。”
“是你待我太像恋人了,从眼神上看也是如此。还有,你的手。”她没说完,嘴就又被堵住。
灯下黑。路灯下并不充足的光线,模糊了她的眉眼神情。只剩下瞳孔的颜色,越发清晰明了。
湖青色的,比过去七年的坚守更深邃,比他们第一次在铃木特快上的初见柔和。
深吻之中,降谷零似乎感到宫野志保才张开嘴唇,做了一个字的口型。
“ki(き)mi(み)”。
——“你”。
他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
满地月光如水,从地面映上来。水中的藻荇是树枝与树叶的影子。他们两个的影子几乎被路灯照成了两个点,又被白色的路灯切割开。路灯也照着玫瑰,如同鲜血一般的红一点点渐变成了暖调的橙黄。他们走着,吻着。无视路人的侧目。当走过那片圆锥形白光的笼罩,又悄悄变成了血红。
红橙交替。直到走到家里。
家里的灯光是白色的,他们手中的玫瑰又重归于温暖的橙色。
仿佛周而复始,仿佛……一个圆满的轮转。
他们家的飘窗可以看到月亮。他望了望银白的月亮,又看向她。她的眼睛像一湾化冰的湖泊,清亮如镜。
也是他的归宿。
孩子们被动静吵醒,惊愕地看着一个陌生但眼熟的男人搂着平时一脸“生人勿近”的妈妈。妈妈的脸色泛红,头发散乱,他们从没见过妈妈如此狼狈。
“你……你不许欺负妈妈!等我爸爸回来你会死的很惨的!他超厉害,是警察!”在小孩子的圈子里,一个当警察的父亲往往是“牌面”的代名词。
“看样子,你教的小孩子很不错嘛。”降谷零笑了笑,“不欺负你妈妈是不可能的,因为……”
他低下头,对着孩子们说。
“我就是你们刚刚说很厉害的那个人。降谷零,请多指教!”
【-FIN-】
4 notes
·
View notes
Photo

【脈輪詳解】根輪——擺脫幻想
根輪在脊椎的底部。梵文中Mulladhara 的意思是"生命的根源"。Mula 的意思是"根",而adhara 的意思是"基本"。
幻想和不切實際的期待會使根輪緊閉。人若能停止幻想而面對現實,根輪則會開啟。
根輪和性,幻想及期待有關。
性,是人最常有的念頭,最常為人討論,也是最常見的寫作題材, 但也最為人誤解,最令人迷惑!人們不是避而不談,就是沉溺其中。性雖深植於潛意識中,卻一直無人能幫助人們了解性的真諦。人們需要重新建立對性的認識。
人們對性的理解如此有限,像是人走在暗夜森林中,而森林某處有陷阱。人對性避而不談,如同不知道陷阱設在何處,無法避開;人沉溺於性,好比明知前有陷阱,卻毫不考慮的跳進去。這兩種情形都不是明智之舉,那人們該如何是好?找出��阱,繞其道而行才是上策。
性,一直是個禁忌的話題,只能私下討論。父母親從不跟孩子討論性,主要原因是父母自己也不了解。所有的問題,人們都需要尋求專家的意見,否則得到錯誤解答,而徒生誤解。
一則小故事:
媽媽收到兒子學校老師寄來的一封信。老師信裡寫到,孩子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而常寫錯。媽媽馬上帶兒子去看眼科醫生。醫生幫小孩檢查過後,寫下處方——剪頭髮!
這是個有趣的例子。現實生活中,如果一開始就找對人問問題, 會得到正確解答;如果只是盲目聽從所謂的"權威",其建議毫無用途,只是浪費時間。更糟的是,人們把這些"權威"建議, 傳承給下一代。多年以來,人們以奉其為圭臬,打破傳承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跟隨大師學習時,大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除人們心中既有的定見,惟有如此,大師的教誨才能深入人心,帶領人們認識真正的自己。這是項艱鉅的任務,因為人們已十分熟悉既有的模式, 不覺得有何不妥。
回到我們的主題:什麼是性?性是一種極具創造力的能量,是一種冥想的能量。因為性,世界因而存在。
印度愛經(Kama Sutra)- 是本有關性技巧的書,它的作者瓦司雅那是個僧人,他終生獨身。瓦司雅那悟道之後,某天回家探望母親。母親問他,如果他真的悟道,應該對世間所有的事都能有所見地。瓦司雅那同意母親所說,問母親想知道什麼?母親說:"你一出生,我就知道你會終生獨身。你不可能有性經驗。你能告訴我你對性的看法嗎?"瓦司雅那笑了笑,對母親講解愛經。
有人曾問瓦司雅那,是否跟權威人士談論過性的議題。有這樣的疑問是很自然的事。我想你們之中有很多人私下對我也有過相同的疑問。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來說明瓦司雅那的立場。
有個電工清楚你家裡每個房間電源開關,也熟悉牆壁裡的電路。如果電路發生問題,他能判斷問題可能出在哪,輕鬆解決問題。因為他了解電的原理。然而,你每天可能開關電源50 次以上,卻對電路一無所知。我說的對嗎?
我們大多數的人都只懂得開燈關燈,所以有時候會不小心觸電。��使我們已經為人父母,甚至是祖父母,對性可能還是一無所知。我們長期受荷爾蒙的影響,不管是電視或是其它媒體,都以各種方式呈現慾望。我們看了這些節目,覺得自己徹底了解愛跟性。
只有真正了解性的人,才能傳授人們性的技巧。
多年以來,印度因土地富庶遼闊而幾經掠奪,但都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傷,社會秩序終究能恢復。但是印度舊時的導師制度(Gurukul system)廢除之後,導師不得傳授愛經給小孩,這對印度社會才是真正的打擊。人們因不了解性的真義,而追逐慾望。
你們有沒有看過人下棋?只是在一旁看人下棋,往往能看出真正的勝著,但下棋的人卻看不清。有人有過這樣的經驗嗎?你們覺得原因為何?因為觀棋者未陷於棋局之中!
沒有錯!觀棋者無關勝負。壓力只會讓人的心變得魯鈍。惟有局外人,才能給出最忠實的建議。上師是全知的,對所有的事情都能有見地。
所以,性到底是什麼?
生物學上已經證實,沒有所謂百分百的男人或女人。男人有49% 的女性特質,而女人也有49%的男性特質,兩性之間真正的差異只有2%。
人的出生,是由父母的根輪結合而來,所以沒有人是全然的女性或男性,而是同時具有兩性的特質。這也是為什麼濕婆神半男半女的形態。不管我們接受與否,人因同時兼具兩性的特質而完整。為了要有完整的人格,人們必須接受並適時的表現出自己個性中陽剛或陰柔的一面。但這可能嗎?人們真的可以表現自我?
譚崔瑜珈中對於性有很完整的解釋。在譚崔的經典裡記載了濕婆神對帕瓦蒂提出的一段有關於性的對話。祂們的見解雖然是在五千多年以前提出,但是仍然適用於今天的生物學。
人一出生,就被社會歸類成男性或女性,並期待表現出的行為合乎性別。因為社會規範,男孩子不能表現出溫柔的一面,女孩子也不應該有陽剛氣。所以人從小有一半個性中是受壓抑的。
七歲之前,社會規範對人的影響還不算深,因為小孩子還沒有性別的意識,而保有完整個性。小孩多以自我為中心,無憂無慮。小孩子真是美好,一看到小孩,人們就會高興起來。
到了七歲左右,小孩子慢慢感受到社會約束。男孩子不准玩洋娃娃或辦家家酒,女孩子不准玩賽車或火箭。即使在衣著打扮及個人用品上,男孩子多是藍色的,而女孩則是粉紅色,我說的對嗎?
在過去父母的責任只是養育子女。孩子到了四歲左右,父母會把孩子交給導師(Guru)教導。孩子7 歲時,導師會先敎孩子印度經典作為啟蒙。如果在十四歲之前,有人有靈性上的經驗,導師會傳授他們婆羅經,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書。此外,還會傳授愛經中的性學相關知識,人們以此能學習家庭生活。在二十一歲前能悟道的人可以體驗當僧人,其餘的人則開始學習瑜珈經典。小孩子在導師的愛跟帶領之下成長。
今日在社會的嚴格要求下,小孩壓抑不為社會接受的那一半性格,天性受到損傷。去了另一半的性格,小孩忽然覺得無所適從, 開始向外尋找失落的另一半。尋求自我滿足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天性。男性不知不覺開始尋找自己失落或壓抑的女性特質,希望尋得替代品,以取代自己失落的另一半。男孩和女孩相互尋找,性就是這樣開始的。
七歲到十四歲,是孩子跟父母最親近的時候。從父母身上,小孩建立起理想異性的典範。對小男孩而言,受壓抑的天性由母親取代,而小女孩則是由父親取代。
所以父母親是孩子心中的英雄/女英雄,這幾乎相沿成習!這樣執著的追尋,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上所說的戀母及戀父情結的基礎。男孩期望自己的妻子能像母親一樣照顧他,而女孩則期望先生能像父親一樣給她安全感,因為父母留給子女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即使成年後與父母親的意見相背,還是無法抹去父母在心中的印象。
到了十四歲,小孩的身體日漸成熟成為青少年,社會規範不容許跟父母親像兒時般親密,活動也多了起來,不像小時候花那麼多的時間跟父母相處。青少年開始向外繼續找尋自己的另一半。現今可能早於十四歲,因為他們從小看電視或上網變得早熟。
小孩以外界及媒體上的形象為基準尋找另一半,媒體因為深知這一點,所有的廣告都充滿了性暗示,採用極具吸引力的男人或女人為產品代言,即使產品與其毫無關聯。幾乎所有的摩托車廣告中都會出現女性- 事實上有幾個女人會騎摩托車?不管是什麼產品,總有個面帶微笑的女士大力推薦;去買東西時,人們不假思索的挑上推薦產品,卻沒有想到這位微笑的女士可不隨產品附贈!媒體從人們壓抑的慾望中獲利。
所有的媒體都只是在販賣夢想。人們收集所有的夢想,在腦子裡想了又想,希望藉此滿足自己的慾望,但這就像吃鹽止渴一樣, 到頭來只是更渴,不是嗎?如果人們了解這一點,廣告就毫無立即或無形的吸引力。當然人們還是會看看廣告,了解一下市場上最新的訊息,不過不會上當。
媒體帶給人夢想,但另一方面社會又不停的壓抑人們。社會愈壓制,人的夢想跟慾望越強烈。社會能壓制的只是表面,卻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好比修剪樹枝卻仍保留樹根,樹只會長的更茂密!拜各類媒體所賜,人們在心中建立完美異性的形象。人們從不同人身上擷取精華的部位,鼻子、眼睛、個性等,建立心中的完美形象。我們都會在計算機裡剪剪貼貼,不是嗎?
到了二十或二十一歲左右,對媒體的認同感逐漸消褪,但是完美異性的觀念已經深植內心。在現實生活中滿懷期望的找尋理想對象,覺得對方"會是"什麼長相,"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接下來的幾年裡,人們不停尋找理想人選,談了一次次戀愛,最後卻都以失敗告終。少數聰明的人終於覺悟,知道夢想不能成真,但大多數的人仍不停尋尋覓覓。
一則小故事:
一個90 歲的老人從早到晚坐在海邊看人。有人問老人為什麼每天都坐在海邊。老人回答說:"我想找個老伴!" 問話的人頗為意外,接著問說:"怎麼年輕時不找呢?" 老人回答說:"我從30 歲開始找到現在。" 問話的人吃驚的說:"你想找什麼樣的女人?"老人說:"我要找個完美的女人。""你一直都沒找到?"這人接著問。"我遇過一個女人,她各方面都符合我的期望,不過我們處不來。"老人說。
這人問為什麼。老人回說:"她也想找個完美的男人。"
事實上,人們希望對方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自己期望。尋尋覓覓多年,忽然遇到一個人,遠觀好像各項條件都符合:心裡的理想人選要喜歡綠色,這個人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綠色的。再仔細一看, 他穿的果真是綠的,終於找到完美的人選!
墜入愛河就是如此。人們總說“墜入愛河“,不說“由愛河升起"。其實一切不過是荷爾蒙作祟,人們卻以為這就是愛。事實上, 人們將心裡強烈的渴望投射在他人身上,卻只選擇自己想看的部份。墜入愛河的人覺得世界綠蔭處處,仙樂飄飄。生活像首詩, 多年的尋覓終得告終,人們開始寫詩,為對方作畫………
只要彼此保持距離,一切都很美好,對彼此投以無盡的想像。但距離慢慢拉近,發現對方穿的其實是淺綠色,但你不以為意的繼續過日子,最後終於發現對方其實喜歡黃色,從沒穿過綠色衣服。人們無法接受幻想破滅,開始編織一個個藉口,自我安慰說:" 生活本就不盡如人意。"
人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智慧才能面對現實,無法面對時總是用藉口逃避現實。最後彼此面對面時,發現對方穿的竟是白色衣裳而不是黃色。想找喜歡綠色的人,但怎麼對方喜歡的是白色!這就是幻想與現實的差距!
一則小故事:
某人從三樓滾了下來,一直滾到馬路上。路人趕緊跑過來,關心的問:"你一定摔的很疼。"某人回答說:"摔的時候不疼,停下來才疼!"
人們若對戀愛不是太認真,保持距離還會心存幻想,不需面對現實。只有在想安定下來拉近彼此距離,把戀情維持久一點時,問題才會發生。人的幻想越多,需要更久的時間才能覺悟,而受的傷害也愈大;幻想越少,愈不會貨比三家,麻煩也愈少。如果不心存幻想,人們會較容易遇到自己的心靈伴侶。結婚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心靈伴侶。
要了解沒有人能符合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因為那並不切實際。完美形像不過是拼湊得來,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到頭來那隻是個幻想。由周遭的人尋找靈感,建立心中的完美形象,其實並無不妥;但是如果只從媒體找靈感,媒體本身都已受慾望所害,如何能給予人指引或安慰?這樣的愛終將以痛苦收場。人們覺得受騙上當,直覺反應是把發生的事怪到別人頭上。能夠怪罪別人嗎?錯還是在自己身上,因為自己滿懷期望,而把期望加諸在他人之上,所以誰該負責?
有些例外情形是因為對方行為反常,以致必須決定是否繼續跟對方一起生活。我所說的理論,並不適用於這樣的例外狀況。我所說的是很多人家中的實際情形,夫妻雙方都很正常卻家庭不睦。雙方都不願正視問題,解決問題,只會將問題巧妙的隱藏起來, 自欺欺人。受傷時應該是馬上處理傷口,但人們卻用金碧輝煌的外衣包裹傷口,告訴自己並沒有受傷。這真是再愚蠢不過!如果你們了解我所說的,就該停止幻想,面對現實。
一則小故事:
某人送朋友一隻小狗當結婚禮物。三個月後,他在街上遇到朋友。"新婚生活愉快嗎?"他關心的問。
"還不錯,只是有點小小的改變。"朋友回答說。"什麼樣的改變?"他好奇的問。"一開始,你送我的狗對我狂吠,而我太太會幫我拿報紙。現在狂吠的是我老婆,狗會幫我拿報紙!"朋友淡淡的說。
蜜月期後就天地變色?難怪只有蜜月,而沒有"蜜年"的說法。不到兩星期,結婚喜悅就消退,即使娶的是名模,只要半個月就看膩了,因為人又開始有其它的幻想。本該追求的是內在的滿足, 但人們卻對此毫無所悉,不停追求外在的假象。
一則小故事:
有個媽媽傳授女兒婚姻之道:"女兒,聽我說,愛一個人就該終生不渝,這才是真愛。"女兒認真聽著。媽媽接著說:"聽我的勸,我是經驗之談,畢竟我結了三次婚!"
人們擅長給別人建議,卻不善於接受建議。每個人對愛、想像, 幻想都有一堆道理可講,但是自己還是不停的幻想。如果人們能學會接受現實,那也還好,但人們真能就此罷手?人們總試著想改造對方,以符合自己心中的形象,這對感情是最大的傷害。佔有對方,改造對方,像改造其它東西一樣,人們畢生致力於此, 永無止境。
一則小故事:
有個油漆工有天跟朋友談起工作上的事。"有一天,有個女孩帶著一張藍黑相間的色卡來,要我依照這個顏色,粉刷樣品屋。
我憑著多年經驗,拼命想要調出她要的顏色, 她卻怎麼都不滿意。"朋友問說:"最後調出來了嗎?"油漆工回答說:"我運氣好,趁著她講手機時,把她的色卡顏色給改了!"
如果仔細觀察每一對夫妻,會發現他們都想改造對方。建議你們結婚的時候,可以送對方鑿子跟槌子當結婚禮物,不用準備婚戒!
另一則小故事:
某人跟朋友有天晚上一起喝茶。他跟朋友說:"我想跟我太太離婚。她已經六個月不跟我講一句話了。"朋友勸他說:"我建議你三思而後行。你再也找不到這樣的老婆了!"
人們一直想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個符合自己心中形象的伴侶。這樣的理想人選並不存在。只要拋開心中的想像,人們有無限的機會。
如果你還單身,停止幻想,你會找到人生伴侶,而不是夢中情人。挑選對象時謹記在心,你是要跟對方過一生,而不是幾個月。不要一時衝動,這是一輩子的事。就像你現在很想買黑色牛仔褲或藍色T 卹,但要知道頂多半年它們就不再流行了!
如果你已婚,也請你停止幻想,才能跟另一半建立真正的感情。如果總是想要改變對方,則無法建立真正的感情。如果開始改造對方,你以為已經改造成功,但是你的想像力又往前推進,還要繼續修修補補!改造工程永不停歇!
心中仍存有幻想,不會有一段真正的感情,即使跟對方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同一個房子裡,因為自己仍活在幻想中,而無法直視對方,無法跟對方一起生活。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心裡存有幻想, 卻覺得老天在懲罰自己。
如果你還未婚,停止心中的幻想,你的心會平息下來,不再受荷爾蒙的影響。如果失去另一半,也請停止想像,你將不會因寂寞而苦。
盡量不要讓孩子看電視。如果只是欣賞裡面的音樂跟舞蹈,這倒還好;但是小孩會把看到的記在腦子裡,內容,情緒等等。短時間不會有問題,但是這些記憶都會儲存在根輪— 它是性能量的中心。再細微的暗示,根輪都能接收到。過多的期望會干擾根輪,讓根輪緊閉,會希望他人或是電視節目中的人物來滿足自己的期望,或將自己的期望及想像投射在他人身上。
根輪緊閉,跟外在環境無關,也跟單身與否無關,而是跟內心完整與否有關。追求自我實現,才會停止向外尋求內在被壓抑的另一半。能自我實現,與有沒有異性一起生活並不重要;如果無法自我實現,即使已婚,還是會繼續受荷爾蒙的影響。這一切只不過是告訴各位,人應該由內尋求人生圓滿,而不假外求。
能自我實現,不管是已婚未婚,心都能保持平靜。在婚姻生活中, 仍能保有自己,這才是真正的獨身主義。但是人們多反其道而行, 脫離現實生活��刻意獨身,結果只是讓自己更壓抑,更神經質。
但是上師,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心裡有完美形象……
那是因為你們很少內觀。人們造訪世界各地,卻從不拜訪自己的心。你們知道人大約80%的能量都被鎖在根輪裡。其實人不需要刻意增加脈輪的能量,只需重啟脈輪,體內能量的流動就能足以改變生活。
如果靜觀自己,會發現痛苦的原因,是所見與心中所願不盡相符。心中所願就是自己希望擁有的完美形象。至少從現在起,試著帶著自覺內觀,看自己如何解讀所見的事物。對所見之事,先試著接受它的原貌,不要先做任何的判斷。你會發現,你的心巧妙且不著痕蹟的影響了你對事情的見解,所以你覺得所看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夠完美。
梵文中有兩句話,教導我們現實的真意:Dhrishti Shrishti和Shrishti Dhrishti。Dhrishti Shrishti的意思是看見世界的原貌,接受並擁抱它原有的模樣。Shrishti Dhrishti的意思是以你喜歡的方式看世界,你可以為它上色,或投以無盡的想像。前一種方式能帶給人們平靜的生活,而後一種方式只會讓人痛苦。
某人跟我說:"家裡只有我跟我太太兩個人,卻還是不得安寧!"我告訴他:"誰說你們家裡只有兩個人?其實有四個人"這人呆住了。
我向他解釋:"你自己,你心中的完美女人,你太太,還有她心中的完美男人,加起來不就是四個人!只要你們彼此都不再想心中的完美女人或男人,看會有什麼改變?"這人聽完,安靜的離開。
上師,我們在其他的人際關係上也遇到障礙,比如說父母跟子女之間………
是的。所有的人際關係中都存有期望,沒有例外。父母想雕琢子女,而子女想改變父母。父母希望子女實現自己未完成的夢想, 希望子女能成為醫生或工程師。為什麼不去了解並幫助孩子實現真正的願望?這對孩子有莫大的幫助。孩子跟你頂嘴時,表示他已經是個大人了。要好好跟孩子相處,花時間陪他,跟他聊天, 當他的好朋友,發掘他的志向,給他最深的愛跟信任。把孩子的雄心視為理所當然,幫他達成。
很多小孩告訴我:"我爸爸要我當醫生"或是"我爸爸要我當律師"。如果小孩自己無法決定,問父母該怎麼辦,父母可以觀察孩子有哪些天份以及能力,提出建議,但不要強迫孩子接受。父母也要給孩子足夠的空間,相信孩子已經成熟到可以做出決定, 並清楚的告訴孩子,做了決定就不能歸咎他人。孩子需要清楚知道自己該負的責任。
人隨時準備要改造他人, 不管是親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來滿足自己的期望。身邊的人也是如此!人們彼此可算暴力相向!
今天回家的功課,我要你們寫下來,理想中的完美先生、太太、父親、母親、孩子,朋友……應該是什麼樣子。任選跟自己切身相關的五種人,寫下理想中他們的形象應是如何。對自己誠實以對,我保證,你們會發現,不知不覺中你們的想法都受到媒體的影響。看電視節目時,喜歡上里面某一個角色,這個角色對你來說如此真實,不知不覺期望現實生活中周圍的人,也能像劇中人一樣。
你們知道嗎?人們甚至覺得"理想導師"也該符合特定的形象?理想導師通常應該是個滿頭白髮,留鬍子的老人,就跟書里或電視影集裡看到的一樣!所以他們看到我,無法接受所謂的大師居然是個年輕人!所以我跟你們面臨相同的問題,我要先改變人們對導師的刻板印象,才能為人接受!
可是大師,有時候我們必須糾正對方……比如說在管理員工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必須改變對方,要保持理性,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不會過了頭。想清楚自己對員工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有替代方案。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糾正對方。不管手中的權力有多大, 都要小心行使。所有的能量都是上天所賜,即使是自己的怒氣或貪欲,如果能心存敬意就不會濫用。
你們會亂花錢嗎?你們不會,因為知道得來不易。如果請人做事, 要花十個盧比,你會多付一個盧比嗎?但是盛怒之下,人們常常過度反應。如果有人犯錯,讓你損失十個盧布,但你大發雷霆的程度,好像自己損失了五十個盧布?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未經思考就發脾氣。如果經過思考,人不會反應過度,事後也不會有罪惡感。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人們不應該因為發脾氣而不安。如果感到不安,表示自己未經過理智思考,而讓怒氣沖昏頭。人們可以藉此衡量自己是否能控制脾氣。
一則小故事:
一次,一個浪跡天涯的苦行僧,經過一個村子,村民向他訴苦, 說村里有蟒蛇出沒,弄得大家雞犬不寧。
這個苦行僧以跟動物溝通著名。所以村民懇求他勸蟒蛇放過村民。
苦行僧苦勸蟒蛇,蟒蛇也答應不再傷害村民。幾個月後,苦行僧經過同一個村子,看到蟒蛇渾身是傷奄奄一息。"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受的傷?"苦行僧問道。
蟒蛇邊哭邊答:"大師,我答應你不再傷害村民,一直到今天我都信守對你的承諾。可是原先怕我的村民,看我變溫和不咬人了, 就趁機攻擊我,每天折磨我!你看他們把我整成什麼樣子!"
苦行僧答道:"我的傻朋友!我只勸你不要咬人,並沒有說你不能嚇嚇他們?"如果脾氣發對地方,次數恰到好處,成效非凡!知道自己為何發脾氣,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很多人跟我說:"大師,我很愛我太太!我是因為愛她,為了她好才要她改變!因為這樣,我們才會吵架!"
我的回答是:"你其實愛的不是你太太,而是你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你愛自己心中的假象,而不是你太太,所以只有在太太符合期望時,才會愛她。如果真的愛你太太,她在你心中就是完美的;如果愛的是心中的假象,你會想改變對方,以符合自己的期望。
事實上,人們大多愛上的是自己心中的假象,而這是夫妻失和的原因,也是親密戰爭的開始。你和你的愛人像是最親密的敵人,形影不離卻隨時保持警戒,常常想要支配對方。兩人敵意極深,卻覺得這是親密的表示。真正的親密,是在對方面前能完全放鬆。
上師,你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完全接受對方,包括他犯的錯?
不是這樣。接受這個字眼,聽起來有譴責的意味。你說接受對方犯的錯,聽來像是在抱怨。好像是說:"還能怎麼辦,只能照單全收。"不!我的意思是,欣然接受對方的原貌,這跟勉強接受不同。勉強接受對方,只是一種妥協;欣然接受則是無條件的打開自己的心,而不抱任何期望。
要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上天賜的禮物,要帶著感恩及謙卑的心接受。如果能做得到這一點,會啟動根輪中所蘊含的極大的能量。喚醒根輪,就像是觸動了你內在一股源源不斷的能量。這股能量,原本因為自己有太多的想像,期望和貪欲而閉鎖,重新啟動,對創意的產生、事業、生活等有莫大的助益。
不僅如此,家庭會更和睦。家庭本該是美德之居,卻被紛爭所據!我說的對嗎?家庭常有紛爭,是因為我們想改變彼此。如果你雕琢的是一塊木頭,或許能雕出美麗的模樣或家具。但如果雕琢的是人心,只會帶給對方創傷。
一則小故事:
有個人,請我為他的離婚祝福。我告訴他,我只為婚姻祝福,不為離婚祝福。
我問他為什麼要離婚,希望能幫忙排解。他告訴我:"上師,今天早上我叫我太太端杯咖啡給我。她卻潑了我一身。"我有點吃驚,跟他說不值得為這樣的小事離婚。
他繼續說:"上師,你有所不知。她今天潑倒的是咖啡,明天可能是強酸。"我嚇了一跳,告訴他說:"阿亞,你怎麼會這麼想呢?你太太只是一時又急又氣,才打翻了咖啡。到頭來洗衣服的人還是她!"
他回答說:"上師,我們結婚時,按照習俗,新人要從三桶水里找到預先藏好一隻戒指。那時候,她的指甲刮傷了我的手!"印度的婚禮習俗,為了讓新人更親近,會玩這些小遊戲。這個人居然記恨十年前的一件小事。我跟他說:"阿亞,你這麼會記仇, 沒有人能跟你一起生活!"
人們常做以下兩件事:把吵架的經過告訴別人,要別人評理;分不出誰是誰非,就繼續吵,證明自己是對的。人們99%的爭吵, 都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所以如果認為自己的太太是個愚婦, 怎麼看都覺得她愚不可及;如果覺得做什麼事,你的先生都要過問,不管你先生做什麼,你都認為他是在干涉你。如果已心存成見,就無法真的了解另一半。
人只看自己願意看的部份,這就好比肚子餓的時候,只想找餐廳吃飯;殺狗前得先告訴別人這是只瘋狗才下得了手。改變自己的態度,如此一來對身邊的人、事、物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一則小故事:
有個人走進警察局,抱怨他老婆已經三個小時不見人影。警察問他:"你能否提供你太太的基本資料,如身高體重等。"
這個人回答說:"這些我都不清楚。"警察接著問:"你記得她離開家時穿什麼衣服嗎?"這個人回答說:"這我沒注意,不過她把狗帶出門,這我倒記得。" 警察問說:"你們養的是什麼狗?"這人回答說:"我們養的是大麥町,牠的斑點是灰色的,不是黑的。大概50 磅重,尾巴是純白的,上面一點斑點都沒有。脖子上帶著棕色的項圈,上面有條銀鍊。狗的名字叫斑斑。"
警察回答說:"這就行了。我們會連狗帶人��起找回來!"
夫妻之間相處,剛結婚的前幾個月可能還有新鮮感。剛開始的幾個月,忙著幫對方打分數,之後彼此疏遠。其實並不了解對方, 但是手頭上有這些分數就夠了。夫妻之間相處,就靠著手上的這些分數,但是這些分數跟實際並不相符。原來的兩人之家,變成四人之家。
誠實的問自己,有多久沒有看著自己另一半的眼睛,跟對方說話?應該很久了吧。婚姻生活剛開始時,一切都很美好;慢慢的,日子變的平淡無奇,這都是因為自己的態度。因為你沒有給對方進步的空間。你急著改造對方,而不想多認識對方。
事實上,結婚幾年後,夫妻雙方就對彼此視若無睹,而只對心中的假象感興趣。結果呢?就像前一個報案的人一樣,對自己太太的一切毫無頭緒!這還只是表面的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你對一起生活的伴侶全然不了解,你心裡想的,只有你的理想伴侶。
在接下來的一天,要下定決心,重新認識自己的伴侶,就像兩人初次見面一樣。對於對方的所言所行,都要有全新的見解,但不要驟下結論。充滿愛意對待對方,即使對方說了一些話,惹自己生氣,也要帶著愛意,專心聆聽,冷靜回應,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爭吵。這麼做會為彼此開啟了一種新的相處模式。你會赫然發現都是因為自己原先的態度,才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你當然可以說對方也有錯,但是你有能力改變彼此。只要改變自己的心態,你能做的其實更多,對方自然也會跟著改變。
一則小故事:
有個人走過墓園,聽見裡面傳出很大的哭聲。他覺得應該停下來一下,看是否幫的上忙。他走進墓園,看見一個人對著一個墓碑大哭不止。這個人不停的哭喊:"你為什麼要死?你為什麼要死?"路過的人見他哭的傷心,也覺得很難過,走近問說:"先生,我很替你難過。去世的是你的夫人嗎?"哭墳的人回答說:"不是。死的是她第一任老公。"
因為心中的幻想與現實不盡相符,感情才會造成創傷。更糟的是, 人們一次次的戀愛,幻想著下一個人能滿足他們的想像。交往一段時間後,如果發現對方不如想像中完美,就換個人交往。從來沒有想過,也許不是對方不夠完美,而是自己的想像出了問題。人們沉溺於自己的想像中,覺得現實生活才是虛假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如此。惟有活在當下,人們才能感受喜樂,才能了解原來自己一直活在幻想裡。
現在的年輕人,愈來愈不願容忍彼此,而輕言放棄婚姻,這多麼可惜。社會需要深層的覺醒。人們在感情中已經習慣互相指責, 卻忘了一個巴掌是拍不響。先別管別人是否需要改變,改變自己, 可以幫助自己還有其他的人。
如果熟讀愛情故事,你會發現無法長相廝守的人,才會過著所謂幸福快樂的生活。
一則故事
關於一對永遠的愛侶。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決定要分住恒河的兩岸才能永遠相愛。每個星期他們划船相會,之後各自返回。他們決定這麼做是希望見面的時候雙方心平氣和。因為他們只能相聚幾個小時,每次見面都充滿新鮮感,而相聚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貴。
所有永遠的愛侶,不管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牛郎或織女,他們從未一起生活。如果他們一起生活,這些愛情故事只怕要改寫了。問題在於現實生活並不像電視裡的愛情故事一樣,有著背景音樂,很容易讓人進入幻想的世界。音樂有種魔力,能融化人心, 讓人變得脆弱易感。電視裡所有的場景,特別是愛情故事的場景, 都有背景音樂,讓你沉醉其中,你全然被電視情節所迷惑。
現實生活沒有背景音樂!用想像力寫詩和用生活體驗寫詩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需要想像力。但後者卻需要有實際生活體驗。記得一件事:另一半是上天所賜。心中的假象,怎麼能跟上天的傑作相提並論!上天的傑作必然勝出。
今天的社會,充斥著大量的色情刊物、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無盡的墮落。人們以各類劣等的替代品,滿足自己的幻想。色情刊物並不能滿足人們的性生活,只會讓人有更多的幻想,更墮落。但人們卻難以抵擋幻想。要了解:只有意志薄弱,沒有無力抵擋;如果有足夠的智慧,人可以抗拒任何誘惑���
上師,你說人要忠於自己。但實際生活中我們怎能隨心所欲,我們需要為家人跟社會而改變。
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問題。你說:"上師,我必須配合他人。"那我問你:"為什麼不讓其他人來配合你?"沒錯,現實生活中人們彼此依賴,沒有例外,但要知道極限在哪裡。人們即使相互依靠,也要有獨立個性!意思是:了解彼此需要空間。在不干擾對方的情形下,努力充實自己的生活。
我沒有什麼絕妙好計……如果我能靠唸咒,解決所有的夫妻問題,我該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人!
上師,為什麼我們不能幫其他人開啟根輪,幫助他人擺脫心中的期望?
你打算怎麼做?能做的,是確定自己拋開心中的期望,如此一來,"四人之家"至少可以減為三人!如何改變對方……有的婚姻諮詢師甚至建議用催眠的方式!我覺得這樣會干涉對方的自由,這是不對的。
有天我讀到一個醫學案例,有個女人想要讓她先生的脾氣變好, 你們可能也讀過這個案例:芝加哥大學正在進行一些實驗,在人腦中植入電極,藉此完全控制人的脾氣。他們當時徵求自願者參與實驗,有上百個女人強迫他們的先生參加。
實驗後有72 個女人回頭要求校方說:"請把電極移除。我要我先生回復原來的樣子。這些女士異口同聲說:"生活無趣極了!以前我們至少還會吵架,還算有交集;現在他完全不注意我!"
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關注。行為心理學家說,正常的人,沒有吃東西可以捱過90 天,可是缺少他人的關注,撐不過14 天,就會發瘋!"事實上,人們忘瞭如何彼此相愛,彼此關懷。愛為人所遺忘!彼此唯一的交流就是爭吵!我想即使你今天坐在這裡,抱怨自己的另一半毫無感情。如果另一半變的感性起來,你又會回頭抱怨,要他們回復原來的樣子。
根輪最大的功用在於一旦開啟,能解決人們一半的問題。連簽名或摘花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一首關於坦米爾聖人的歌,歌裡頭提到,他們從樹上摘花,樹一點都不覺得痛苦。意思是當根輪開啟,脈輪裡的能量換轉換成愛,人會變的敏感而充滿愛心,樹亦能感受得到這份愛。
性愛如果像碳,真愛就像是鑽石。性愛像污泥一般,而真愛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性與愛兩者本質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於,人們知道如何昇華自己的愛。只要放下自己的期望,就能釋出極大的能量!
我希望你們今天回家後都能試著做以下的練習:
坐下來,把注意力集中在根輪上。你會發現自己的根輪是緊繃的。
接下來的5 分鐘,心裡默想,如果你的另一半曾經冒犯了自己, 不要怪罪對方,完全原諒對方。全然接受對方,給對方最深的愛。
只要5 分鐘,你會發現根輪完全放鬆。如果能徹底改變自己心態, 你能想像會有如何的轉變!你會感到內在能量源源不絕。
你現在的生活方式,就好像自己有十萬盧比,卻有九萬塊鎖了起來,用僅剩的一萬塊生活,難怪你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人們的能量因為用錯地方—— 用來生氣,用於性愛……,以致脈輪閉鎖, 而沒有足夠的能量應付每日生活所需!
只要能打開自己的根輪,生活會更充實,思考會更清楚,對事情了解更深入,計劃更周詳。你能感覺到內在能量持續運行,進入一個從未體驗過的境界。會發現其實自己的另一半以及周圍的人,其實是充滿感情!
要知道:天堂跟地獄並不真實存在。在地圖上也找不到,而是存乎己心。身在天堂還是地獄,全憑自己是否願意改變生活方式。心中滿是期待,猶如身處煉獄!不管到哪裡,都承受重擔,逃脫無門。兩個人相處時,只是衝突倍增,無法協調。
為什麼要背負如此的重擔?放下它。想想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浪費在改造他人,以符合心裡的期望。放棄改造別人不是比較容易些?即使只用10%的精力來冥想,生活都會因此變的更加真實。
生活應該是自覺而自在。每個人都能更有自覺。一切存乎一心!
上師,我們如何拋開慾望,讓愛滋生?
終於有人提這個問題……慾望跟憤怒一樣都具有很大的能量。事實上,不了解什麼是慾望,又如何轉化?人做什麼事都是以慾望為出發點,即使只是撿起一支筆,或拍拍小孩的頭。性跟慾望因為媒體的不良影響過度被渲染誇大,而人們對性與慾望的壓抑也讓爆發後的結果加劇。當自己的慾望不為他人接受而遷怒對方, 報上才會讀到年輕男孩求愛遭拒,憤而對女孩潑酸這樣的新聞。
首先要了解的是,社會將人分成不同層次。但人並無貴賤高低, 差別在於內在能量能否提升。��下種種道德規範的人,其實都是假道學,心裡都隱藏了許多慾望。因為不敢或羞於面對自己的感覺,而以道德家自居。設下各類道德規範,人因此分高低貴賤, 社會因此不安。如果總覺得自己不如人,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 就無法提升自己。
所有的事愈是抵抗,阻力愈強。其實只需要提升自覺,情形自會有所轉變。不要過度分析,這只會讓自己人格分裂,內在衝突不斷。分析的技巧應該運用於科學研究,而不是心靈成長。人們習慣分析所有的事,無法停止。如果有人想評斷你優劣與否,你只需記得人都是萬物的一份子,並無優劣之分。只有在忘卻此一真理時,對人才會有差別之心。
只有愛是真實的,慾望的產生是因為無知。慾望可昇華為愛,就像煉金術可化銅為金。人原始的慾望,也可以昇華為崇高的愛, 這是最極致的修煉。
我跟各位說一個我在喜馬拉雅山區遊歷時,發生的真實故事:
我在喜馬拉雅山時,習慣隨意行走。那段時間我遇過不少修行的人。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衣衫襤褸修士,帶著一堆糾結的鎖,面容兇惡。他是那卡派的修士。不知為何我受他吸引,向他走去。我跟他一起走了幾天。他每天都抽著水煙,我看著他抽,覺得很好奇。
他把兩個銅幣丟進水煙壺,抽了一會兒,把煙筒倒乾淨,倒出兩個金幣!他到市場上把金幣換成更多的銅幣,重複之前的過程。我問他是怎麼做到的。他沒有回答,只是把水煙壺遞給我。
我從來不喜歡煙味跟酒味,倒退幾步。我跟他說:我到喜馬拉雅山是為了學習冥想及悟道,我對抽菸跟金幣毫無興趣。他看了我ㄧ眼後說道:"本心開悟,就能煉銅成金“。我當下無言。他開玩笑的在我臉上噴了幾口菸。接下來的三天我都感受到極深的喜樂。
煉金術旨在煉銅成金。煉銅成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首先去除掉金屬裡的雜質,加入催化劑,加快製程,原本的破銅爛鐵,成了價格不斐的貴重金屬。而人們內在的修煉,是為了將原始的能量, 轉化成較高層次的靈性的力量。如果熟悉內在的修煉,煉金術只是小事一件,像小孩的把戲。
我告訴你們我的故事是希望你們了解內在修煉的意義,而不是要你們學習煉金術!外在世界的煉金術並無特別之處,內心的修煉才能真正的成就自己。
人必須將原始的慾望轉化。人的原始慾望是動物的本能;但動物之間的慾望十分單純,與外在世界無關。但是人類的慾望卻不單純,而且帶有罪惡感。過去的經歷,不是使人羞愧而慾望大減,就是讓人們慾望倍增而沉溺其中,到頭來只會讓人更有罪惡感。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讓原本單純的慾望不再純粹。
你們會發現滿足自己的想像會有罪惡感。所以性讓人有罪惡感。小時候家人最先灌輸的概念是罪惡感,所以人長大後習慣替自己安罪名。人們如果想要控制對方,會先讓對方有罪惡感,讓對方覺得在某方面不如人,然後對方就會按照自己的話去做。人們在成長時應運用智慧,逐漸建立自己的人格,罪惡感自然會遠離。但是多數人盲從規矩,而錯誤也代代相傳—— 父傳子,子傳孫。
所有的美容產品,都不停的傳達一個訊息:你不夠完美。人們開始以自己的外表為恥,於是買了一堆美容產品來使用,而被廠商所控制。人們用美容產品,會有罪惡感-"我費盡心力,就只是為了這些?"每次完成某件事,人們最先有的是罪惡感。
我們回來探討人的慾望。幻想讓人沉浸在毫無意義的生活。電視、網絡、書本等等……讓人們產生許多幻想,在腦中根深蒂固。人若生活在幻想中,即使結婚了,也還是滿腦子幻想,而不關心真正生活中的伴侶,因為對方只是幻想的替代品。人們原本單純的慾望受到污染。
人沉溺於自己的幻想中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人們不敢深入探索自己的慾望,總在最後關頭放棄,卻又一再回頭,而且渴望得到更多。如果勇於深入探索,終究能擺脫慾望而使自我成長。
早年人們在四十歲之前,就能不為慾望所擾。人們心中沒有復雜的假象,與自己的伴侶十分親近。所以年紀雖輕,卻能以成熟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慾望。能深入探索慾望,而不為慾望所擾。不需刻意擺脫慾望,慾望自然遠離。
印度的婚禮中,新人會當眾唸一段美麗的詩文。妻子對丈夫說:
"願你成為我第十一子。"丈夫對妻子說:"願你成為我第十一女。"真正的意思是,他們結婚十一年後將視對方如子女般。看著自己的孩子,心中總是有無比的喜悅。跟自己的另一半之間的關係,必定經過無數的轉折,才能在彼此相對時覺得像看著自己的小孩般喜悅。
人們的痛苦,在於不了解心中妄念何來。惟有了解原因才能擺脫。生活能不為妄念所苦,已接近靈性的生活;如果不懂如何擺脫妄念,過的只是物質的生活。世上有兩種生活方式- 有自覺的生活,以及沒有自覺的生活;得道之人的生活,以及愚人的生活。
人為內心的慾望幻想所惑,不管身在何處都不會快樂。這就好比人一心想坐在椅子上,所以不論坐在地板上或墊子上都不高興;有人給了自己一把椅子,又想坐國王的寶座;坐在寶座上,還是覺得不夠享受。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自己有的只是單純的慾望,當深入探索慾望時,不帶有任何的罪惡感或過多的想像,人們終能擺脫慾望。如果心中夾雜太多的幻想,終將無法擺脫。拋開心中根深蒂固的妄念,好好愛惜及欣賞自己跟他人的身體。人的身體本該充滿喜樂,只因執著於自己的妄念而無從感受。修煉的第一步,要先拋開對自己及他人身體的妄念,除去慾望中的雜念。
懂得欣賞自己的身體,福氣自會降臨。所有皮膚的疾病,大多是因為厭惡自己的身體,或缺乏自信所致。但人們並不了解原因為何而遍尋良方。問題的根本其實就是心裡多年累積下來的偏見。人們總是羨慕別人的身體,想要跟別人一樣。如果能愛惜自己, 欣賞自己的身體,人會內外皆美。
早年人們的想法十分簡單,因此心中幾乎沒有成見。從外界接受越多的假象,心中的成見就會越深。若能擺脫這些假象,就能夠愛惜自己及他人的身體。而愛惜之心在個人修煉中,如同催化劑, 能將慾望昇華成愛。
圖西達斯所寫的史詩羅摩耶那中記載,西達公主走進父親傑那卡的宮廷中,宮廷中所有人,包括偉大的聖哲瓦西塔都起身向她致意,因為她散發出一種清新脫俗的優雅。
譚崔派別有一種修煉的技巧。每天早上醒來,以愛惜的心輕撫全身,使心靈與肉身合而為一。
要記得:暴力不是解決的方法。我們常常談到社會中或國家之間的暴力情形,卻鮮少談到家中的暴力,以及對自己身體及心靈施暴。我可以這麼說:家庭是暴力的起源。
你可能會說:"上師,我們在生活中從不使用暴力。"你們覺得自己很友善不粗暴,但我所謂的友善跟你的定義不同。可以試著觀察自己:走在街上或在自家的花園裡,是否無意中會攀折樹木花草,踢著腳下的石頭,拉扯藤蔓等等。這些都是暴力的行為。想想看:自己是無意中攀折花葉,還是有意?你能分辨兩者的差別嗎?告訴我,你是真的對萬事萬物和善嗎?
試試在走進花園時,充滿敬畏及愛意的仔細觀察一朵花,全新感受它的美以及與它的生命連結,像照顧新生寶寶般呵護它,感受內在湧現的情緒。不管看待任何事,都要保持覺知。人因為靠潛意識行事,對周圍的事暴力相向而不自知。如果能保持覺知,能看出萬物有無限的美,便能愛護萬物。
人們如此虐待自己的身體:暴飲暴食,造成消化系統的負擔。極需休息,卻熬夜折磨自己的身體;明知抽菸喝酒對身體有害,卻照做不誤。這難道就是愛護自己的方式?人們一定不喜歡自己的某部份,才會虐待身體。停止談論外界的暴力,開始重視自己內在的暴力,外在的暴力自然會平息。人們隨時能指出他人的缺失。但自己有數不清的缺點,該如何自處?
某人對我談起他的家人。他太太是個律師。我問他:"你太太需要出庭辯護嗎?"他答說:"不需要,她在家裡有的是機會!"
人們隨時指責他人,為自己辯解。其實只要消除心中的雜念,自然不再需要辯解。牢記對自己或他人有所助益的話。對他人的身體及心靈表示和善,這是最實用的修行。修行不是只有定時敲鐘, 對著財神爺祈禱發財,而是能隨時保持善念,財富自然降臨。
人們以為需要舉行各種儀式,才能得心中所求,其實不然。就算一天念"阿彌陀佛"念了一千次,卻無心改變自己,這跟念"可口可樂"一千次的效果是一樣的!儀式的目的,主要是能深入了解自己,藉以改變自己,物質方面的收穫自然降臨。如果能對他人和善,有耐心並堅持轉變,終能體會愛,而他人也會因為你的轉變而改變跟你的互動模式。你的內心將充滿喜樂,冥想算是大功告成。
人的本質是愛,而性是兩人深層的結合。問題在於,真愛長久以來為慾望所掩蓋,真心無法結合,結合的只是肉體。人際關係多半只是表面功夫,膚淺的事極易動搖,除非有深入的根基。這道理再簡單不過。
慾望使人盲目,讓人慢性中毒。愛也算是一種慢性中毒,卻能帶領人們到深層的自覺,那是至美的境地。愛和慾,像是兩個極端。只要能讓人進入深層自覺的經歷,都是一種冥想。如果只能讓人停留在下意識,則不具任何意義。人可以藉此判斷目前的經歷是否對自己有益。
還有一件事:如果愛得夠深,不會起忌妒之心。忌妒是因為擔心自己的愛不夠深,終會消逝。如果愛的夠深,何須忌妒,何須恐懼?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對自己的伴侶不信任,是因為彼此的關係只是表面,是建立在幻想跟慾望上。如果只對一個人只有浪漫情懷,這並不真實。生活本就是浪漫的,萬物都有浪漫情懷, 全看自己是否能感受。
用理智表達自己,是一種智慧;用心表達自己,是一種慈悲;用身體表達自己,是一種能量;雖然無法表達自己,卻能真切感受自己的內心,是一種福分。
能達到這種境地,人們不需仰賴外力才能得到喜樂,而是隨時都能感受到內心喜悅的共鳴。如果能跟他人分享,喜悅更是倍增。如果覺得跟某人特別親近,不一定要真的接觸對方,只要跟對方感到契合,就會感到喜悅滿足。
這種契合的感覺,不會因為分離而稍減。真正的感情,是彼此深深的契合。不了解這層道理,而想盡辦法跟對方綁在一起,以為這就是感情,這樣的感情基礎其實極不穩固。即使用盡心力維持, 最終只是彼此折磨。
有人告訴我:"上師,我想住在靜心會所裡,我在家裡一點都不快樂。"我常說,在自己的"四口之家"都不快活,跟一百個人住在聚會所裡會更不快樂。你們把聚會所當成翹家者的庇護所嗎?
要了解:回家與否跟外界無關。不論外在環境如何,如果能時時保持喜樂,隨時都有回家的感覺;如果不了解這一點,不管到哪裡都一樣。我曾經待在八尺見方的圈地裡,當時的喜樂與今日坐在講壇上並無二致。這種隨遇而安的能力,在於自己能否了解:快樂跟外在環境毫無關聯。
狗不停啃著骨頭,啃到嘴裡流出血來,還以為血是從骨頭里冒出來的,而啃的更賣力,不停舔著血水。再啃下去,這隻狗一定會覺得痛。人也是如此,以為是外在的世界讓自己痛苦或快樂。沉溺於這樣的想法只會越來越悲慘。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上師,我們要如何保護孩子,不讓他們面臨類似的問題呢?
坦白說,人無法掌控所有,也不可能控制孩子跟社會的互動,不過有些事在家裡可以做。誠如我之前所說,不要壓抑孩子另一半天性。讓孩子以各種方式充分錶達並親身體驗,不要太在乎性別的差異。讓孩子保有自己的天性,給予適當的機會探索自己。小孩還沒有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時,在自己的世界裡十分自在。
你可能注意過小嬰兒會玩自己的生殖器,或把大腳趾塞進嘴巴這一類的事。這只是表示,小嬰兒在自己的世界裡十分自在,而且充滿了愛,他們在自我探索,樂在其中。可是我們卻予以阻止, 說做這些事是不對的。其實應該讓孩子自己探索。
小孩盡量穿一件式的衣服,而不要穿上下分開的兩件式。兩件式的衣服容易讓孩子意識到身體分成上下兩部份。一段時間後,會慢慢忽略自己下半身。如果要描述自己的長相,通常都只說得出上半身,而完全忽略下半身。
即使可能要冒點風險,還是要讓小孩保有自己的天性,自由探索。小孩能完整表達自己,不要壓抑他們。孩子不懂做表面文章或偽善的事,不像大人都精於此道,心中有諸多顧忌。大人從來不曾完整的表達自己。
讓小孩自由的使用雙手。我們常不准小孩使用左手。為什麼不讓小孩使用雙手?這並沒有錯。此外你們可能注意過小孩子都喜歡轉圈圈,這是他們集中精力的一種方式。人只有在臍輪清淨時, 才能自在的轉圈圈。
小孩如此天真無憂,所以轉起圈來毫不費力。可是我們讓孩子自在的轉圈嗎?看著小孩轉圈,自己也開始頭昏起來,趕緊叫他們停下來,告誡小孩說:"趕緊坐下!這樣轉圈對身體不好。"聽我的建議,讓孩子自在的轉圈圈,只要墊張毯子,讓他們跌倒時不會摔傷。
還有一件事:不要灌輸孩子任何的恐懼,讓孩子自由自在,爬高爬低,摔個幾次也無妨。如果常常阻止小孩,將來孩子可能會有多種恐懼,例如懼高,怕黑…等等。久而久之就會不敢面臨挑戰或嘗試未知的事。
上師,你說世上沒有完美的伴侶。那為什麼結婚前要算命合八字呢?
我所說的,可能會推翻所有的算命的理論。算命本身並沒有問題, 而是人們運用的方式既愚蠢又毫無意義!要知道: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應該最清楚箇中好壞,但是人們卻對自己的生命一無所知,轉而請教他人,人的智慧何在!將生命交到陌生人手中, 任由其決定自己的人生,這表示人們不知道如何過自己的人生。人應該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人們如果問我未來會如何,我會告訴他們—不要叫我預測你們未來。除非需要有人幫忙計劃未來,才來找我。意志不堅的人, 才會需要預言。
古代的算命是一種純科學,其中有很多道理。讓我告訴你們,算命是如何演進。在過去的導師制度下,小孩子跟著導師學習,導師會利用算命來判斷小孩子的性格,態度以及才能,而決定學習的方向。早期的階級劃分,並不是以出身為依據,而是以人的個性以及天份為基準。
導師指導小孩之前,會先看小孩有什麼天份。有智慧的孩子,有成為婆羅門的潛力,將學習吠陀經典。如果個性勇敢,孔武有力, 將學習武術。如果有多重技能,則學習做生意的技巧。如果樂於從事固定工作,將學習為民服務。這四類工作同等重要,同樣受人尊重。
古代算命是作為判斷人的依據。你們周圍的人幾乎都未盡其才。有醫生天份的人,成了工程師;該當工程師的人,卻從事僕役, 所以社會才會一團混亂。一個適合從商的人卻從事靈修,結果把靈修當成一門生意來做!
所以古代算命,是一門經過驗證的科學嗎?上師?
我最怕人們問到這個問題。我一說是,人們會瘋狂迷戀算命。明天早上就會有一長串人,拿著自己的八字在我面前排隊,要求我幫他們預測未來。不要太在意算命的結果。有人問予耶克有關算命的問題,他的回答相當合宜:"吃好,睡好,多運動。身心都健康,就不需要擔心占星的結果!"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會仰賴算命。
上師,所以相信算命的人,都是意志薄弱的嗎?
雖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大多數是如此。即使平日再聰明不過的人, 也可能一時誤信。有人問我:"上師,如果我戴上各類寶石,會因此運氣變好嗎?"人們怎麼會相信寶石帶給你好運!人不只具有意識,而且具有神性!我無法相信我傳授人們的學問,足以讓人主宰自己的人生,而人們只關心要戴什麼寶石!
你們可能聽過耶堤大師。他是一位真正偉大的導師,一個真正的悟道者。他第一次出國旅行,出發的時刻,根據行星的位置推算, 是所謂的大凶之時。有人問他:"上師,你為什麼挑這個時辰出發?"他回答說:"你們何等愚昧!我的能量足以影響行星的運轉,行星的方位又怎麼會影響我呢?"他的勇氣令人敬佩。惟有大徹大悟的人,才有如此的勇氣。
我傳授給你們的學問足以影響你們周遭一切,而你們又何須在意行星的位置會對你造成任何影響。只要學習冥想,就不會受任何事影響。
但算命已經是我們價值觀的一部分,上師……
所謂的價值觀和意識其實是同一件事。如果意識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需要價值觀來指引,不需要刻意遵守任何規則。所有的美德、紀律、精神層面都以意識為準,精神層次自然能提升。
人們聽到意識或心靈提升這一類字眼時,常常在沒有嘗試過任何冥想技巧,或其他提升自我意識的方法時,就會認為這一切與自己無關。人們要先排除"心靈提升大不易"的想法。
心靈提升是如此容易, 追求財富,需要努力, 追求名聲,更須努力,追求自我實現,只需要活在當下!
如果能讓自己進入一種幾近沉靜的狀態,就能進入至善至美之境!我所說的沉靜,不是一般所說的身體的懶散,而是一種心理上的放鬆,人能全然放鬆,就能真正進入心靈層面。進入心靈層面,說不上難或簡單,只是一種概念。難易與否全憑自己的感覺。活在當下,需要特別做什麼嗎?只要內觀,對自己的精神層面有信心,適度的冥想,這就夠了!能放棄原先的思���,進入心靈層面不是件難事,你會有信心的跟自己說:"我做得到!我也是有意識的。"不需刻意擺脫,原有的價值觀自會遠離。
人們不敢拋開現有的價值觀,是因為無所依歸。一旦放棄現有的價值觀,就是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壓抑已久的慾望一下傾巢而出,結果只是大亂!人們在潛意識裡有所顧慮,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如果持續練習冥想,潛意識會淨空,屆時即使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也不會有任何慾望,心將如明鏡一般。
—— 本文摘自尼希亞南達上師
著作《Guaranteed Solutions》第五章
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原地主菩薩的干擾(二)
以下為三則分享:
分享一
在一個月內莫名其妙胃痛了好幾次,N次吃完飯後胃就開始不舒服,還以為是吃飯過快造成的。每次胃痛我就立刻吃胃藥和止痛藥舒緩,但總感覺怪怪的,以前都是一樣的吃飯速度,為什麼最近胃痛的這麼頻繁,一痛就只能靠服藥止痛?
兩週前發現多次起床時腳無力,偶然在上班的路上走著走著,腳也是莫名其妙的酸痛及無力。還以為是吃素營養不良,或是因工作忙碌常有一餐沒一餐,吃飯都不準時而造成的。某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對先生說:「最近怎麼腳都無力?」先生立刻回答:「我也是!怎麼那麼巧,我們兩個都一樣腳無力?」這時先生立馬說要填單請示。
請示一:最近兩週腳常發軟無力,先生也是如此,請示是否有干擾?
請示二:最近一個月多次胃腸不舒服,請示是否有干擾?
開示一:有一位原地主菩薩干擾,誠心持誦《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各230遍,待持誦完畢,來信專案迴向超度其投胎轉世。
開示二:同一。
看到慈悲的佛菩薩開示後,當時並不覺得很驚訝,因前幾個月在台中家,每次休假回台中總是不好睡,有請示過此事,佛菩薩一樣開示出有兩位原地主菩薩出現需要我超度,當時記得有位師兄看了我的心得,也有去請示外面租房的不順,佛菩薩開示出租房處有位原地主菩薩干擾。台中家的兩位原地主菩薩,在上個月初我已迴向圓滿了,休假時回台中家,發現晚上睡覺不會像以前那樣睡了又醒,現在一覺可以睡到天亮夢也少,也比較容易入睡,回到家裡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心浮氣躁了。
收到精舍開示,當天晚上下班回家後,我便告訴先生:「台北宿舍也有一位原地主菩薩。」先生怕我壓力太大,無法接受又多了經文各230部,還特別跟我分享他看到《阿伯的話─現場開示精華節錄》:「修行人經唸久了會產生光環,光芒越大則會遇到兩種情形,一是外道會來干擾阻擋修行,二是家中往生者或鬼道眾生會前來求您超度,但這是好事,要堅持下去。」
感謝這三位原地主菩薩的出現,來告訴我祂們需要超度,這也是我的榮幸。如果我沒認真誦經及修行的話,祂們應該也不會來找我吧!看來我與原地主菩薩有緣,只有我能夠超度祂們,幫祂們在阿賴耶識中種下佛法的種子,下世投胎轉世等機緣成熟,也能夠遇上佛法,踏上修行之路,才能有機會脫離苦海。
分享二
爺爺分家時,當時在村子有兩片地方可以分給二伯和我爸來住,然後通過抓鬮決定。一片地方挨靠著大街,位置比較好,蓋房也比較容易,而那片地剛好被我爸抽到。後來爸爸努力打拼,攢了一些錢後在此地蓋了一棟樓房,也就是現在所居住的家。但自從搬到這個新家,我就一直感受到房屋磁場不是很好,家人氣氛比較不合,且經常會吵架。
後來有幸認識精舍,通過請示,開示有一位原地主菩薩干擾,須誠心持誦《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各130遍,待持誦完畢,專案迴向超度其回陽世子孫處接受供養,不要再干擾。雖然經過後世子孫的多層轉賣,但其祖先未修行,靈還是一直執著此土地不放,無法離苦得樂。後世的人住到這裡才會被干擾。期許自己努力圓滿此開示,超度原地主菩薩回到陽世的子孫家中接受供養,不再干擾我們。
分享三
大伯母二嫁到我們大家族當大媳婦,有帶一位小男孩過來,卻莫名生了一場大病很小就離開,後來與大伯父婚姻裡育有三子三女。大伯母思想封閉,認為自己生的孩子是最優秀、最好的,常誇、也寵壞兒子女兒們,容不下妯娌間的小孩。
大伯母的弟弟來自故鄉宜蘭鄉間,初到臺北無人相識,北上依親,投靠姊姊也就是大伯母。大伯父為人好,當初口頭允諾這塊土地讓舅子一家五口蓋房安居,且無立白紙黑字,讓在異鄉的他無後顧之憂安家定居。全家住了數十多年,工作勤儉賺進不少錢財,夫妻在不遠處買新房搬離此地,後來此屋空置許久。
這房子大伯母的弟弟有房屋所有權但無地上權,搬離房子同年告訴大外甥(大堂哥),這間房子要去過戶登記在大堂哥的名下。大堂哥人不貪,工作壓著也遺忘這件事,前幾年因病過世,連前幾年往生弟弟的遺產也不為所動,日子耽擱也沒人處理那間房屋。最近,小堂姐因病也暫住那間房子,這位舅舅來探訪外甥女的病況,幾天後很快離開人世間,相繼小堂姐不到幾天也離世了。
我沒進去過那房子,都是在外探頭,只覺裡面就是黑黑暗暗的,燈也不亮。愈想愈奇怪,便照相請示佛菩薩:「小堂姐大病未離世前,她舅舅來看她後,舅舅發生大事也突然過世了,這房子是不是有問題?」佛菩薩開示:「有兩位原地主菩薩。」
俗話說:「有萬年的土地,無百年的主人。」土地是先祖留下來的,先靈捍衛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可以諒解。古早人重情重意,一言九鼎,情意相挺,無白紙黑字立一字一句,現面臨房屋所有權子孫登記的問題,原先的好心好意衍生家族糾紛應該不是先人想見,只是如今人事已非。
(分享完畢)
《阿伯的話-現場開示精華節錄》:「原地主菩薩即是地縛靈,為原本此塊土地的主人之祖先;地基主是土地公所派遣的部下,負責小區域的管理,原地主菩薩與地基主不同。原地主菩薩干擾的原因,係執著此塊土地,但在陽世間的法律來看,後代子孫已將土地轉賣,因此活人(後代子孫)賣地而死人(原地主菩薩)不賣地,需誦經迴向才能化解,使原地主菩薩回到其陽世間的子孫家中接受供養。」
土地傳承,一手過一手,建商收購土地建屋、私人土地、房屋買賣等,在現今的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與保障,然而對於土地或房屋最原始持有人的祖先來說,後代人規定的白紙黑字對祂們沒有約束力,靈只會執著土地、房屋是自己的所有物,後面住進來的人是侵門踏戶,因此會想方設法干擾住進來的人,目的在於將人趕走!
原地主菩薩干擾是很普遍的問題,住到裡面有原地主菩薩的房子,身體會毛病多、意外多、事情多、運勢會被擋掉,總之就是諸事不順、萬事不吉。遇到原地主菩薩干擾只能對其「道德勸說」,迴向功德讓其回陽世子孫處接受供養或讓其轉世投胎,畢竟人鬥不過靈,讓原地主菩薩心平氣和、心甘情願的離開不再干擾,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解決方法。
阿伯說:「修行人經唸久了會產生光環,光芒越大則會遇到兩種情形,一是外道會來干擾阻擋修行,二是家中往生者或鬼道眾生會前來求您超度,但這是好事,要堅持下去。」
修行人修的是慈悲心,慈悲心是「無我」,無我才能展現出大愛。原地主菩薩生前因為沒有修行,所以看不破、放不下,縱使已往生數百年、數千年,靈依然執著於自己喜愛的人事物,緊緊攀附不願離開,這是非常可憐的一件事情!遇上原地主菩薩干擾,務必抱著正確的心態,相逢自是有緣,不要歸咎於都是唸經帶來的麻煩,也不要認為原地主菩薩就是來找麻煩的,好好跟原地主菩薩稟告,說您願意用唸經功德超度祂們,請祂們在您唸經時一起來聽經,一般說來,原地主菩薩感受到您真切的善意與善心,干擾的力道會減輕許多。
再者,人跟靈的磁場本就不同,即使原地主菩薩無心干擾,但家裡同時住著無形眾生,對人的身體多少都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除非您是租客,不想承擔過多的責任,那麼只能摸摸鼻子,搬走就好,不然為了以後的長治久安、安居樂業著想,還是遵照佛菩薩的開示,老實做、老實唸經,想辦法唸經超度祂們,與祂們結善緣。
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定數,有緣遇到了便想辦法解決,今生種下的善因,是在替未來累積善果,遇上原地主菩薩干擾,務必抱著在做好事的心態,即使您沒有想讓對方回報的意思,但功不唐捐,點點滴滴依然會記錄在您的功德簿中。總之,不管是各人業力干擾或原地主菩薩干擾,妥善規劃好各人的時間,堅持再堅持,凡事努力去做,隨緣盡份,問心無愧。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韋馱菩薩
南無伽藍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
0 notes
Text
【北欧组】E♪♪erkoppen/知蛛
*长文预警
*18+ 预警
房间里的另一头响起了开门的声音,迎面走来的女人,她匆忙张开的双臂很平静。男人走到门侧,女人折回门口,双臂里抱起一个少年。男人好像鼓足了勇气似的,直直地便杵在原地,就那样把手伸着。女人回头等候回应,躺在手臂里少年伸头张望。可男人伸出的双臂却发着隐隐的抖。
“让我来抱阿冰吧,西尔维娅小姐。”
男人喊出声来,音量大得能恰到好处地给自己一些自信。
“我不要!”
少年的头在西尔维娅的双臂上向着男人伫立。被称作阿冰的少年刚把话讲出口,话却碰着了男人眼里微弱的凉意,于是手捂到嘴边,好像说话的舌头被凉着了,因此接下来的话,多少带了些愧疚的凉意。
“我的上半身还可以动,我想在家里坐轮椅。”
“你不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吗?”被叫做西尔维娅的女人轻轻地问。
“我想一个人看会书。”
女监护人什么都看见了。她的眼角夹着疲惫,却是微笑的。
“别和老师较劲了,阿冰。”
提诺从西尔维娅的手臂上接过阿冰的时候,她正用食指帮阿冰拭去眼泪。不知是困乏还是有一种悲伤,各式各样的小孩向来是流眼泪的高手。提诺第一次学着女主人西尔维娅的姿势抱起他的时候,并没有掂到一个普通的十三岁孩子应有的分量,好像连他的体重都在抗拒自己。
一年前的那个秋天,阿冰——或称他的全名,艾斯兰·弗洛克松,在提诺闻讯赶来之前,就在他面前从一个半成年人那么高的爬杆上像一片布一样掉了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周围包绕的是学校的枫叶山林,和他坠落大地时那不合情理的回响。有那么一瞬,提诺就那样同后来从爬杆上逃窜而去的小朋友们一起看着艾斯兰的脖颈渐渐变青变红,红得刺眼,随着入秋的呼唤,绿色的青春像学校里漫山遍野的秋日红枫一样,染上了妖冶的鲜红。提诺来时的那天,班上很热闹,走时的那天,班级也是一样地热闹,好像他从来不是师长,艾斯兰从来不是朋友。
他抱着艾斯兰往沙发走去。这并不是一个宽阔的家、也并非一个窄小的家。提诺用脚丈量着这个家的宽度:三步并作两步,便可从艾斯兰的房间行至沙发、两步并作三步,便能从沙发行到完全开放式的厨房,折返一步便来到餐桌。再折返一步就又是沙发。艾斯兰独自住在靠门的一侧的走廊,也就两步宽,餐桌则在窗的一边,紧紧挨着。在门与窗的中央,往更深处安眠着的,则是房子的主人两口的起居室。这是个碗橱与装饰画同样昭彰的家、这是个拖鞋与地毯同样匍匐的家、这是个倦怠无力与兴致勃勃同样纡尊的家。
艾斯兰被放在靠门的沙发一头,提诺自己坐在向窗的沙发一头,他们之间的纽带便是这一双发臭的下肢。提诺低头沉默着,牵拉起流浪在人间的腿,把手掌合上脚掌,向艾斯兰的方向扳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艾斯兰在沙发上的活动便是这沉默的牵拉,好像划着一艘湖水里游泳的红船。
“累吗?”
“累。”
艾斯兰的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被他从额头抹在手里的汗被重新攥紧,他在忍受。他眯起眼睛,模糊的光影里看见提诺的眼里兀自闪亮着。在他下肢瘫痪后的一年里,这个前班主任的眼里总是闪着浑浊的光,艾斯兰的流汗没有停止,提诺眼里的光又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于是他干脆把眼睛闭了起来。
“还累吗?”
“今天到这吧。”
直到电视机也打开,五彩斑斓的画面从荧屏上显示了,他才示意提诺调转方向,直到他调着频道,头枕在提诺的腿上,一切训练才终于停止,他能好好伸出手掌来,看着自己抹到手里,流作一片狼藉的汗了。艾斯兰就保持着他枕在提诺的大腿上的姿势,任凭自己撒了很长一会沉静的娇。许是已经从疲倦中缓过神来,他开始同提诺搭话。
“...你想看什么。”
“我?”
“又在播基督教堂被烧掉的新闻、摆了台后,这个台是雕像公园的广告...就是那个福洛格纳公园。我不想看。你想看些什么就看些什么。遥控器给你。..现在我不喜欢看电视。”
“诶,可是,过会我得给西尔维娅小姐帮手做菜。要说看电视...”
“这个台在播《动物世界》、你看这个吗?前几天上生物课的时候,你放过这节目,也讲过这节目:蚂蚁和蚜虫、它们是特别的一对共生的关系。我还以为你会喜欢呢...因为你从前上科学课的时候也讲,只是没有今天讲得这么复杂。我以为你经常看这个节目,要不就不会把今天的课讲的这么难懂。”
“是更抽象了些、因为还加了些中学的内容。”
“但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
“你能感兴趣...我很高兴。那时的科学课,是要给克里夫先生代课。他年纪已经大了。”
“你的科学课比尖老头讲得好。连奥拉夫和比约恩那样的笨蛋都已经知道了蜘蛛和蚂蚁、蚜虫们的区别。”
“奥拉夫他,不是不喜欢听课,只是,要比起上课来,他更想和别的孩子聊天,他性格比较怕孤单。比约恩虽然不喜欢听课,但是他的父亲是养蜜蜂的。他喜欢昆虫。世上没有笨孩子。”
“可是他们的成绩,那时确实总是比我要差些...”
提诺的五指顺着艾斯兰柔软的发,顺得他比从前更加疲倦了。蜘蛛从屏幕那头出现的时候,提诺感到枕在自己大腿上的孩子的肩膀轻颤了一下,频道便从这头换到另一头去。艾斯兰的头被放进沙发里的时候,他的眼睛便从电视机前挪开去、跟着提诺的腿去了厨房。
刀在响。
“阿冰的成绩总是比同龄人要好些。比起职高,他更适合普高课程。他仍有一个聪明的大脑。”
碰开羊排骨的刀声与摞开白菜的声音秩序井然地码放在对话的间隙之中。两个人的手在贴近案板的低空碰了几碰,羊排骨与白菜便齐齐整整地码放在锅中。
“这一年来,彼此都辛苦了。尤其是您。”
“您客气了,这是我职责所在,不管是替您家分忧,还是为我的学生分忧...我刚刚收到回应,有一所中学愿意接收阿冰作为他们的特别学生——他们会保证阿冰同每一个挪威公民的孩子一样坐在课堂里学习,只要那时能够到场参加他们的期末考试,拿到让他们满意的成绩...按阿冰目前的恢复状态和学业表现来看,那并不是难事。请您放心、我会尽我所能...”
“可您的酬劳,同您付出的思虑实在是不成正比。”
“同我在职时没有两样。”
“连现在阿冰的入学事宜,也是由您去沟通的。”
“过程算不得顺利、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贝瓦尔德先生也帮了不少忙。况且,阿冰是聪明的孩子...他应得的。”
“可您这时,不该连佣人的活也一起做了...”
“因为您也让我借住在这里。”
锅子在火上烧着最后一煲汤。西尔维娅的一双手洗得白净透亮。窗外刚刚隐隐亮了一亮,她的一只手还在水流下受着洗,另一只邀过提诺的双手来,用指腹细细揉搓着他沾了羊肉血珠的手。
“那毕竟是我的过失,否则我便不会离职。况且,倘若是真正的佣人的话,本该连最难打扫的客厅也一并清洁,尤其是沙发,因为阿冰平日里在那上面锻炼还流汗...应该很容易变得臭烘烘的。”
西尔维娅搓洗的手停了一下,柔软的水流在四只手掌之间积蓄起来。
“您本应该在高中、甚至如果实习期结束,应该回到你的故国芬兰,或是转到挪威的大学去教书,或者是按你原先的计划去,继续读完你的硕士——...。”
西尔维娅喃了喃,水龙头最后洒出清水几滴,只剩两颗指腹在湿润里互相厮磨。
“在挪威,这可不该是双佣人的手啊。”
“可做老师的总要先学会做佣人,您应该要懂我,科勒夫人呐。”
“别叫我夫人,我可不过三十出头、比你可大不了几岁。”
提诺·维那莫依宁看见西尔维娅似笑非笑的嘴角,那笑容只是刹那一瞬,就转眼消失在她疲惫淡漠的眼中了。她往耳朵上别了一下头发,他觉得那笑容一定被她别到那头发之后,顺着滑进发梢的森林里去了。
从阿冰在学校登记的名字里,或许可以推断出她嫁作人妻之前的名字,可她对外总是称其丈夫的姓氏,工作以外做的也全是妻子的家事,这让他有时会忘记她只不过是艾斯兰的姐姐。可那点缀着她丈夫的家姓,却总像她时而蓬乱,时而柔顺的金色长发一般,在她雾色的姓氏前如妆般摇曳着。她暂时离开厨房,靠在洒满昏黑与霞白的窗边倒茶。热气从茶杯里扑满他的面颊,她穿过热气的珠雾,把一口饮料送到提诺的嘴边。
“先别急着喝。”
在他还未着手打算享用忙碌的馈赠的时候,两片肌肤的热气汇成脸颊间肌肤的暖流。西尔维娅对着他的耳朵说话。
他知道这是西尔维娅要同他说些小秘密,只是在科勒家偶得的每一次双颊紧贴之时都让他的心跳如此措手不及。西尔维娅特有的聊天方式对他来说就像一场社会性灾难。在灾难来临的第一回,当他想说“不行”的时候,无处安放的手被她十指相贴缴械投降,隔着西尔维娅披散开的发帘,他看见马西亚斯·科勒,冠以西尔维娅以本家女主人身份的,真正的一家之主,闭着眼喝着咖啡。他看着马西亚斯的喉结上下摆动,黑色的饮液像流行在喉间的水车一样击打着西尔维娅耳旁微风的节奏,使得西尔维娅���声音也带着一线苦涩,直到马西亚斯一饮而尽的终末,他才终于听清饮料里西尔维娅摆动的双唇。
“今晚,贝瓦尔德·乌克森谢纳要来。”
提诺揉了揉耳朵,西尔维娅的唇就这样同他的耳朵分开,在他的脚步声里热气远去。
“贝瓦尔德先生、他又要来了吗?”
“应该是快了。”
艾斯兰看见提诺从餐桌前走来,边看着大门,边对着漫杯的茶水开始喝,直到喝得茶包都露了底,他便把嘴角抹着了,杯子摇摇晃晃地挂在艾斯兰的头顶。提诺接着伸了些懒腰,指头上还挂着茶杯,随着他的懒腰上下飞舞,最后茶杯落在沙发的靠枕上,他的手肘和下巴也撑在沙发上。茶杯底已干的茶包滑着杯底的水,隔着透明的玻璃在艾斯兰的头顶晃来晃去。他们俩就这样同艾斯兰分享着看电视的快活。
艾斯兰烦了,说:
“提诺,杯子拿开!”
跟在提诺后头的西尔维娅说:
“阿冰,坐起来。贝瓦尔德先生要来了。”
“我来帮你起来。阿冰,来。
艾斯兰翻身的时候,遥控器落在了地上。他的眉头轻轻皱起,连带着瞳孔也一并向里凹陷下去,但他的思虑只是略略地在眼珠上踩出一个浅坑,便即刻往深黑的瞳孔里塌陷坠落,像一朵瞬间枯萎的雏菊。提诺俯下身去抱他,再起身的时候便见到了那双眼睛。艾斯兰在轻声地说。
“我、..我回房间去。”
“不看电视了吗?”关切的是西尔维娅。
“现在我不爱看这个节目。”
频道从这头切到那头来的时候,蜘蛛从屏幕的那头又出现。提诺把遥控器摆了又摆,孩子却只是垂着眼睛。提诺揉了揉胳膊,从电视机前将他抱起的时候,门外飞进一声清脆的邀请函,是门铃。
“我来吧。”
艾斯兰像块肥皂一样滑到西尔维娅怀里。她在这孩子的额头上落下一吻,提诺便目送着他们前往艾斯兰平日的住所里去。他的双臂和这间屋子忽然空了,只有不疾不徐的门铃在屋子里清洗着。他用掌跟抹着额前的碎发,心里笃笃说着别着急,只是这话的声音一旦从喉咙滑进心口,回声便在他的心里荡起一阵频波,和门铃轻轻地和鸣着。他握着门把的手心出了汗。我来开门、我来开门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掌根贴着门把向下一摁。
“Sur-pri-se!”
西尔维娅轻掩上艾斯兰的房门的时候,那充满活力的大喊已力透耳膜,男人和提诺扑了个满怀。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提诺、西尔维娅在哪里?不在这里,看来我只是太想她了...我提早回来了,你今天看起来很精神,和以前一样精神,圣诞快乐!你来自圣诞的国度,我自然要尤其祝你圣诞快乐,是吧,是吧...提诺?”
提诺应和着过分热情的男主人,帮他抖掉肩膀上的雪,换下沾满炸鸡和牛肉味的大衣和帽子。马西亚斯·科勒拍着提诺的肩膀——他足够高,高高地扬着笑脸——然后转身向西尔维娅迎去。
“我回来了,西尔维娅。”
他的唇和西尔维娅之间没有距离,在唇线上精致地挂着胜利者的微笑,勾得优雅,像国王走向行宫。西尔维娅踮起脚尖,伸手扶了扶他被帽子压折的翘发,顺着鬓角托起半个脸颊,又用她特有的聊天方式柔声诉说。
“马西亚斯。谢谢你。谢谢你特意这么早到家。贝瓦尔德呢?”
“圣诞快乐,吻我,亲爱的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向提诺的方向望了一眼,接着周身开始如上了发条的齿轮般向内旋转,齿案一颗颗地向内卡去,卡去,直到他们俩咬合成天衣无缝的机器,使得周围的空气再也擦不出火花为止。他们站在阿冰房门前的回廊,这条被西尔维娅一眼望得到头的回廊,便如静止的八音盒一般,让音乐也停止,让提诺也停止住了。只有如齿轮一般旋转、旋转在门和门槛的夹缝之间的门铁,正在为了扳开这道被提诺的铁臂挂住了的门而向外牵拉的力而从这音乐盒中,擦出了一声——
“吱扭。”
那就是最后到场的贝瓦尔德。
“圣诞快乐,贝瓦尔德!”马西亚斯字正腔圆。
谁都知道今晚马西亚斯·科勒家在忙着准备庆祝圣诞夜,这一向是所有生活在奥斯陆的人家们的传统,不论是马西亚斯家还是奥斯陆人的圣诞夜,���无人提起,却无人忘记。从去年到今年,这是马西亚斯家横遭不测的一年。在滚烫的石油之血从地底向上奔流至挪威地表的每一处毛细血管的时代,在脊髓灰质炎被疫苗彻底消灭、分娩的疼痛永不复发的时代,在解脱了一切独裁者与战争狂人,人们谈论昼夜一般谈论幸福的时代,他们却听说马西亚斯·科勒家的孩子从爬杆上坠落,摔伤了颈椎,自那以后便连挪威人引以为傲的、儿童教育黄金时代的七年级都无法可读,连奥斯陆人引以为傲的圣诞夜都只能在医院度过。报纸是易燃品,可正当他们把愤怒指向那高高端坐在班级金銮殿之上不可一世的实习班主任的时候,他却从那王座上消失了。奥斯陆的怒火被刹那浇熄的时候,没有一个外乡人是无辜的。那班主任是个外乡人,奥斯陆人听说他辞职住进了受害者的家中,听说他现领着极微薄的薪资,干着仆人的差事。这足够了,虽无人提起,却无人忘记。奥斯陆人咬牙切齿地看着马西亚斯家门口渐渐有彩灯亮起,那来自圣诞之国、全然洗净了自己罪过的班主任正在拉起那棵漂亮、高耸的云杉树。
“提诺,进来吧!”
奥斯陆人看见那窄门向外逗留出些许的暖光,从清冷闪亮的圣诞彩灯那里,他们看见欢腾的外乡人,提诺·维那莫依宁,向着门里小跑而去,渐渐与那暖光融为一体,然后在屋内屋外全都融成一片的欢闹声里,门关上了。他们要喝酒了。
“日子是在不断变好的。”
马西亚斯·科勒把扎杯放下。
“你酒喝得太多了,马西亚斯。喝点姜糖水吧。”
重新升高的黑色液面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西尔维娅把一杯饮料递到他的唇边。马西亚斯的双眼自此迷离开来,好像双眸糊了一团粉红的口香糖,上下眼皮扯出的长丝黏糊糊地垂下嘴角。西尔维娅用红色的餐巾纸替他擦着嘴,马西亚斯的话被餐巾纸扑得嘟嘟囔囔的:
“我当然知道我喝得太多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嗝。”
马西亚斯扶着啤酒的扎杯把,仿佛铆足了劲似地往椅子背后仰去,简直要摔在椅子背上成一滩人泥。
“可在前天还是冬至,小傻瓜们。你们知道冬至是什么日子吗?在那一天,太阳到了最南边去,从那一天开始,太阳在逐渐回到北方的怀抱。夜晚是在不断地变短的啦。黑夜最长的一天过去了,我们北欧人正是如此!总是呼唤着黑夜离去,白昼快快来临——”
贝瓦尔德把纸巾递给西尔维娅,让她替这饭桌演讲家擦擦嘴巴。
“西尔维娅啊,你是好女人..我们不坏,我们一直都不坏,日子在不断地变好。从我们过去直到现在,我们有了阿冰,阿冰也长得这么大了——阿冰,你今年几岁了?”
“十三岁了。”艾斯兰费力地切着一块肉肠。
“十三岁了、你本应该要上七年级了才对...命运是何其不公啊,我们没能把你从险恶的命运之中拯救。我听说你的同学们嫉妒你的才华。你的智商怕是有一百五,乃至有一百六,要比历史上的所有人都逼近爱因斯坦——你一定知道他是个科学家。你知道尼尔斯·玻尔吗?他也是科学家。人们常把尼尔斯·玻尔同他相提并论,我从前崇拜过玻尔,但我现在喜欢爱因斯坦...玻尔有脑子,还有一大帮朋友,但爱因斯坦除了脑子什么也没有,却胜过他那一大帮朋友。脑子够了!有脑子的人不应与少脑子的人为伍,因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摧毁你脑子...你是一匹独狼,你应该对那些把你从爬杆上推下去的王八蛋们竖起中指!”
马西亚斯的话没有接着往下行去,便被自己用半杯姜糖水泼灭。他畅快地发出饮用碳酸饮料的声音。咔~
“里面加了蜂蜜吗、西尔维娅...还有杏仁和葡萄干...”
西尔维娅点了点头。
“下一次,放到冰箱里、...更好喝,好喝得很...”
“真是的、你懂什么啊...”
艾斯兰把刀磨得吱吱作响,带着脆骨的肉肠在他的嘴里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把带着刺,烤得焦香发辣的话语在其余四个人面前咽下。马西亚斯又喝完剩下半杯姜糖水,长长从鼻子里出了一口气,这次没有畅快地“咔”,他的皮肤往里皱进去、皱进去。在他眼下的肌肉如口香糖般若有若无地伸张、抽搐后,提诺看见叫马西亚斯的男主人的眉根轻轻下垂,便在左眼里涌出眼泪来。
“是的、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
他把整张脸都埋进空空如也的盘子里,好像脸上真有一张口香糖似的,便呜呜地哭泣起来。艾斯兰用刀叉把盘子划得吱吱作响,似有火星溅出,好像在切一块钢。一只意料之外的手摁住了艾斯兰的拿刀的手腕,提诺也抬起头来,他看见贝瓦尔德已经把眼镜戴好了。
“阿冰、不要这么说你的姐夫。”
“没事。贝瓦尔德。”西尔维娅抚摸着哭泣的家主的背脊,像安抚一匹狗。“他也不该在这几天提这种论调...虽然明天才是平安夜,但今天也是小平安夜了。”
“可日子确实是在变好...不是吗?”
话从贝瓦尔德宽厚坚实的胸膛里传出。艾斯兰没有继续再磨刀叉了,只是埋头喝汤。在一阵微妙的沉默过后,提诺·维那莫依宁感到自己忽然成了目光的聚焦点,还有西尔维娅在冲他露出微笑。他感到脸有些发烫。壁炉里火已经渐渐有些颓势,他的脸却愈发滚烫,于是他吐了嘴巴里的骨头起身,预备去壁炉里加柴,当他转过身去,贝瓦尔德却已经先一步去把温度升高。那火结实地吃了贝瓦尔德一记,火焰便重新扭着腰,从炉灰里懒懒地生了出来,重新在壁炉里安睡下去。
“日子确实在变好的。”
马西亚斯不知何时也从臂弯里露出脸来,却只是头在双臂垒成的围墙上滚了一圈,侧着脸意犹未尽地冲着提诺笑,脸上的泪还没有干,眼神却变得更加清爽起来。
“一年来你实在是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对吧,提诺。你不要害羞。没了你,我们家今年的日子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顺溜...你看,看看这些菜,没有你帮西尔维娅的忙,做不成这样!还有这些蜡烛,摆的多么齐整,多么像圣诞...你是芬兰来客,圣诞的来客,你把圣诞带给了我们!”
“你在来挪威之前在芬兰做些什么?也是做老师吗?西尔维娅说你还在读书...?读的硕士吗?”
“是的、...”
“专业呢?”
“...古生物。”
只剩下壁炉在安静、纯净地燃烧。艾斯兰看见提诺的脸上的红潮渐渐地发起灰来。
“研究史前生物啊、了不起。”贝瓦尔德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你也是一匹天才啊!”
马西亚斯开始拍着他的肩膀,吐着酒味的嗝。
“用错词了,马西亚斯。”
他拍了一阵提诺的肩膀,觉得乏味起来,便又重新趴回手臂里。
“不要搅我的兴...贝瓦尔德,总之就是,很厉害、很厉害!...枉我见过这么多能干的人,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专业!是研究乌贼、长毛象那些东西的吗?博物馆里那样、你们是怎么把它们从一堆泥巴变得那么高大、那么伟岸的?”
“所以我常说。”西尔维娅轻轻地叹气。“提诺他...原本也不应该受雇于我们家,沦落到做佣人的地步。实在是他自己人太好。”
“提诺以前也做过佣人吧?手很巧、虽然说你不是芬兰人嘛...但是羊排做的却很有挪威味,简称挪味——”
“笑话太冷了。”
贝瓦尔德轻轻地点头附和着。西尔维娅接着说:
“就算他自己不那么觉得,但在旁人来看,这几乎就是刑罚。”
她抬起头来,双手向上合成十字。
“去年的同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在医院里忧虑着阿冰的未来,反省着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为何会导致这样惨痛的结果,直到真正的圣诞到来的时候,也如惯常的忧郁一样溜走。阿冰迄今以来的人生,又有多少属于孩子的节日是这样一点点地从我们傲慢的忧虑之中溜走的呢?”
松开双手以后,她从马西亚斯的身边夺去酒瓶,便往面前的扎杯里倒酒。提诺瞪大了双眼,好像那硕大的扎杯里灌满的是他的眼球一般,一颗接着一颗地充满西尔维娅的口腔,直到她的腮帮似乎再也装载不下如此巨量的啤酒以后,她才开始努动自己的食道,每一颗都在她的喉口团成一块球状的皮肤,在她通红的高领毛衣上攒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圆来。
“您是不是喝得太多了、科勒夫人...——”
“随我、这点随我。”马西亚斯嘿嘿地笑着。提诺看见贝瓦尔德站起来,像制止艾斯兰的刀叉一样,用一只手就摁住她的酒杯,在桌上稳稳地刹住瓶底。
“你得听听阿冰怎么想,西尔维娅。”
“...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艾斯兰从汤碗里抬起头,往西尔维娅的方向侧着眼睛。
“她要喝就让她喝——”
马西亚斯还想为妻子辩护几句,西尔维娅却用食指堵住马西亚斯的口,止住了话语的泄露。
“万幸...我们失去了那个圣诞夜,但我们再也不会失去任何一个圣诞夜,因为提诺·维那莫依宁从圣诞之国来了。
世界可被称之为北欧五国的国家之中,挪威、瑞典和丹麦自不必说,他们的历史向来是维京人的历史,是奥丁庇佑海盗的历史,哪怕自称皈依基督,他们的心也从未接近基督。而远在大西洋上漂浮的冰岛,也被迫卷入了海盗的历史。
只有芬兰——我们提诺·维那莫依宁的故土,是圣尼古拉避开了海盗的港湾,向着一览无余的冰海行船,把耶稣基督的教诲带到那里。在耶稣降生的日子里,圣尼古拉像东方三博士一样,向每一个他所知道的孩子赠送着礼物,用善意给养伯利恒之星。
哪怕人已在大地上获得了法律的许可...他在全能的天父眼中也仍是孩子。因此,提诺·维那莫依宁献出了自己宝贵青春中的一年,赠送给了生活在海盗历史之后的奥斯陆,送给我们这贫瘠之家以弥足珍贵的礼物。”
她用那根堵住马西亚斯嘴巴的食指蘸了蘸剩下的啤酒,将身子跨过伏在桌上的马西亚斯,酒珠从提诺的额头滚落,湿润左眼的睫毛。
“你是我们的家人。你可以离职,你可以离开。”
西尔维娅说。
“你离开以后,去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人。”
西尔维娅开始轻轻地唱起圣诞颂歌,马西亚斯轻轻哼着,右手轻轻打着餐碟。贝瓦尔德稍稍迟钝了一下,但却很快转过头来。提诺见他的眼镜里满是温柔与赞许,西尔维娅解开她的头发,将头绳递到他的手里,贝瓦尔德便自若地伸出手指来拨弄着,拨弄出诸多的音符来,数个音符很快堆叠成一首和鸣的诗,不断地堆叠起来。有一声“呜呼”,马西亚斯在双手里拍出热烈的节奏来,贝瓦尔德推了推眼镜,皮筋里便喷出一切的音韵,他们之间即刻展开一场响度战争,这战争把歌曲拍碎又重合,在热烈的餐桌和鸣出一首即兴的原创圣诞金曲,献给看呆也听呆了的提诺。
艾斯兰看见,提诺脖子以上的头开始不自禁地跃动起来。艾斯兰现在低头划拉着铁匙,他抬头仰起脖子痛饮浓汤,他左顾右盼,窗外已经是深得黑的黑,蜡烛从餐桌的这头一直点到餐桌的那头,火光贯穿到壁炉的一头,早已把提诺烤得腹背两面发红发光。涔涔的汗与油滴在碗里,艾斯兰右手发力,餐刀一点一点把黑麦面包的油皮拧进刀口的孔洞里,直到餐刀的铁与瓷盘相撞,击缶,击缶,击成曲末最终的一柄撞针。
音乐戛然而止。艾斯兰觉得自己现在便差站起来了。
“我吃饱了。”
提诺抱着似已沉沉睡去的艾斯兰背向火光,向着黑黢黢的卧房行去的时候,他听见孩子、学生与他所愧疚的对象说出这句梦呓般的低语:我无法忍受了。他感到手臂实在有些酸——许是那滴额间的啤酒已经渗入他的肌肤,他开始喜欢上这家的啤酒味道——因此他靠着墙根稍微站了站,以解酒昏。红色的火映照红色的沙发,餐桌旁的贝瓦尔德在伸出一只平齐的掌来,眼镜的红缓缓抹平在镜片之上,渐渐地便泛起一层粉色的雾,雾下影影绰绰,他往暗处看了一眼。
“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好。”
“关于您提的我可以离职的事情、...还请您再允许我考虑到圣诞节为止。”
提诺打开房门的时候,便又听见那童稚的呓语叩打耳畔。
“你啊,该不会是已经喜欢上贝瓦尔德了吧。”
两盏橘色的夜灯也停靠在客厅的桌面上,贝瓦尔德略略前倾,写满文字的笔记本便上足了暖色的光晕。
“我来帮您整理睡觉的地方。”
“谢谢。”
眼镜被夹在他长而宽厚的指掌���间,架在其中一盏夜灯上,橘色的暖光便蒙了些许灰黑的斑点。提诺看着他从衬衣口袋里夹出一支黑色水笔来,干练遒劲的笔迹蔓行在霉斑的纸张上。
“是瑞典语吗?”
贝瓦尔德点点头,伸手拍了拍提诺的腰,示意的手接着便向下落进沙发,让出一个可供陪同夜谈的座位来。笔没有停,提诺便借着笔迹追看了半晌,好像夜不曾阖上人的双眸一般。流畅的笔迹,在渐渐晕开的墨点前停顿。他的笔在簿上扣着,打着沉闷的节奏。
“你懂瑞典语吗?”
“我曾学过一些。”
“用它写诗的时候,我才愿意写出诗来。”
“虽然一直知道您是诗人,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您作诗、...这是首讲什么...”
“帮我读一读。下面的部分我难以想象。”
贝瓦尔德的头枕着双臂,双臂枕着沙发的扶手,半身是睡进沙发里了。他闭起眼睛,眉头紧到一起,像有些诗还在里面。
“那、请您稍等...有些词有些生疏、..”
贝瓦尔德睁开眼来,一把夺过写满了诗歌的簿子。
“那不用再念了。”
他是忽然地站起身来,把步轻轻地踱着,也不看小簿子了。提诺在背后出了声,声音是有些发抖的。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您不高兴、我也不是有意地冒犯您的诗...您要吃水果吗?”
贝瓦尔德重新看着了提诺的眼睛,这回是平视的了。提诺起初眼里还有些微颤动的水光,不过很快便淡向别处,是有些害羞了。贝瓦尔德轻轻叹着气。
“晚餐桌上,西尔维娅也说过一些讨人厌的话。你怎么看?你记得是哪一句?”
“..我、抱歉...我不记得。”
“你当然不记得。你会记得那种话吗?你们芬兰人,会记得那种话吗?”
奥丁庇佑海盗的历史。这句话像撞击后宏大的钟声一样在提诺的大脑里嗡嗡地响着。尽管壁炉仍然燃烧,但贝瓦尔德这时的表情却冷极了。或许是他也觉得自己的表情有些冰冷,他接着便说:
“我总是这样、...他们不是什么坏人。西尔维娅也好、马西亚斯也好。你也是——况且我每次来到这里,占了你平时睡觉的地方。”他重新坐回睡觉的地方。
“那样反而更好、这样我就能顺理成章地和阿冰挤在一张床上。他需要不时有人给他翻身或者换尿布——从那以后他便没有再睡好过觉,可他总是介意和我一起睡。但是,医院现在也渐渐减少了专人前来辅导的频率...或许艾斯兰渐渐也能够有睡着的机会了。有时他虽然显得成熟过了头,但终究还是小孩子、睡得着的时候,也还是会说梦话。那时我便不愿叫醒他。”
“你喜欢照顾小孩子、我喜欢写诗...”
“这、不一样...。毕竟您是职业诗人、...。”
“算我说得错了。我不喜欢写诗。”
“可是我看过您的诗。您说您不喜欢、但那怎么可能呢...怎么说呢...我觉得竟能在这困难的一年中,读到您的那些充满希望的,文风有如H·豪格一般的诗歌、甚至结识了您本人。在这充满绝望的一年中,已经是我今年莫大的幸运了、...。”
“你读得挺多。我和他完全不像。”
“或许...我不懂。可能有些多嘴了。但您已经是我亲眼见过以诗为生的、最棒的诗人了。”
贝瓦尔德把笔插回衬衣口袋,把沙发坐垫久久坐稳。提诺也这么坐着,壁炉在燃烧,二人有汗烤出。
“谢谢。”贝瓦尔德闭上眼睛。
“可能有些冒犯您了。”提诺站起身来,借着橘色的光,最后抽出一张纸巾来,把贝瓦尔德有些浑浊了的镜片擦拭干净。沙发上靠着半躺的人把眼皮打开一条缝,盯着他擦。
“我、...和科勒太太他们,可能都不太会说话。您或许有只能由自己来排遣的忧郁,我想,科勒太太他们如果知道您对那些话感到不舒服、一定也会同您道歉的。那句话...在我听来也确有不妥之处、..”
手指抓紧了衣领。
贝瓦尔德揪紧了提诺。
愤怒抓住了惊恐。
眼镜还差最后一擦。
“什么不妥?”
壁炉刹那翻腾出喷涌的火星。提诺·维那莫依宁的双臂膨胀起来,眼瞳里的惊恐即将向着彼岸挥出全然正义的暴力机器——他要保护自己。而此刻他想逃避的,那对贝瓦尔德的眼眸早已全无护卫的秘密可言,因为他的眼镜已经被抓在自己手上。刹那之间他想起艾斯兰,那个一年来头脑总是无法规劝身子的孩子,贝瓦尔德此刻庞大的身躯便如同那孩子一般,他紧紧攥着提诺的衣领,他那悲悯的眼无法控制自己庞大的双臂手中的动作。他太过愤怒,以至于他赤裸的双眸之中,竟闪烁着诸多无辜与哀求。提诺背对着壁炉,因撕扯而裸露出的肩膀被热气所烘烤,他却感觉到了凉意,热气从顶撞头脑的眼处慢慢退潮,他冷下来,在与贝瓦尔德赤裸的双眸相对,冷凝的话语便从唇里流出。
“圣诞老人是假的。”
芬兰并不出产圣诞老人,他知道那是一场芬兰人自营的生活骗局。当他书写板书背过身去,将完成的礼物献给他的孩子们时,他们便埋起头,念起又抄写起自己的书来,口里念的与手里写的却始终是地地道道的挪威语。从孩子起,他们便不同这芬兰人一样留恋圣诞老人,留恋驻留与别离,只是低着头,弓着腰,拾起地上遍布的礼物,把笑脸全部奉送给礼物。对提诺·维那莫依宁而言,这俯拾的道理早应在他从父辈接过教育的重担时便全然接受——他以为自己早已抓稳,但当要捧起这颠簸的手把肉,啃噬这一沉默的真理的时候,他的眼泪却无法停止地因为疼痛而流淌——接受圣诞老人的假象。
热气还在持续顶撞着他的大脑,却不再是愤怒与惊恐,而是不断地冷凝成渐渐浑浊的涡流。他的唇早已被眼泪灌满封口,不再有言语的余裕,多余的泪便不断地顺遂着叙述的召唤,重新从眼瞳泄出。
提诺很强,不是因为他随时准备着动手回击眼前的怒汉,而是当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流泪的时候,他便打算努动舌头,重新向贝瓦尔德解释起眼泪与偶然的口误来。但他说不出话来,他以为自己只是因为刹那的情感口不能言,便四下寻觅,直到发觉自己用于解释的嘴唇现被贝瓦尔德亲吻着、用于努动的舌头在交缠的时候,他却没能像镇定自己膨胀的手臂一般镇定自己渴望亲吻的心,当这颗心被贝瓦尔德湿乎乎的舌轻轻撩动的时候,他因为欣喜若狂在贝瓦尔德的拥抱里剧烈地颤抖着,而贝瓦尔德如前,也无辜地、哀求着地颤抖着。
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做如同马西亚斯和西尔维娅之间的,只有彼此的情人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提诺便渐渐使自己平放在火红的沙发上,就像他平日里睡在这张佣人所必然专享的非床之床上一样。在他的愧疚稍微减轻些时,他也渴望与阿冰共享一张床,但他唯有在这火热的沙发上能够全然遁入仅有的昏暗体验,舒展开自己的肢体。那冬日于无人之境燃烧着的壁炉在他的睡前总使自己想起自己的家,与严厉却不失温柔的父亲。于是他向贝瓦尔德展开自己的肢体。衬衫的纽扣已经顺滑到成了他身体的拉链,他希望身上的拉链一直解到两腿之间,但却轻轻把双腿夹紧,伴着贝瓦尔德向下轻啄轻吻的频率轻轻开合着。
他的呼吸渐渐跟上了心跳的节奏,他的感官追上了吻在身体地图上的踪迹,像是一场漫长而色淡的旅行。没有人在沙发上说话,只是壁炉中轻轻开裂的木与柴在他的耳畔回响:
“日子是在不断变好的。”
他像捧起一只生命一样,双手从贝瓦尔德光滑的脊背后捧起他的下巴,一直到头与头、眸与眸再次两相对视。
“我拿灯过来。”
小夜灯中的一半光亮在沙发靠背的平原上一览无余,借此贝瓦尔德能够发现提诺漂亮的眼睛,那眼眸却只是与他的双眸凝视了一会,然后缓缓地合上,等待。或许取而代之的是下沉至面颊的绯红,但在赤红的暖光中,便连那点爱情的余裕似乎都不足为道,只有提诺的声音在陈说。
“贝瓦尔德先生。”他说。
“我在这里。”
“我从以前开始、可能就已经喜欢上您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这里。每到您回家过节的时候,西尔维娅说你是从采风的地方回来的。每见到您一次,我的心里都对您更加尊敬一些、..。”
借着灯,他看见贝瓦尔德期待的笑意爬上唇角、可那像是一双在看着的眼睛吗?提诺在犹豫着,因为那眼眸瞪着它所怒视的对象要裂出血管来。他的眼只是怒视无法被性爱覆盖的地方,好像他再有一秒便不再打算继续了。但他的手却始终温和地替代起微笑的唇吸吮着早已充血的乳,在贝瓦尔德的双眼所看不见的地方爱抚。
“你这同性恋。”贝瓦尔德吐出一句。
提诺几乎到了羞耻的地步,因为贝瓦尔德的那目光很烫,烫得他感到自己的热情还亏欠了很几分,他应更坦诚些、更解放些、更感恩些。他想说出话来,可贝瓦尔德在帮他系上纽扣,衬衣被涨满,酸胀起来的乳在衬衫上撑起乳白的峰顶。提诺惊叫不好,因为衬衫把他的乳重新勒得疼痛,胸口闷起来了,他轻声哀求着。
“这样不喜欢吗?”贝瓦尔德也只是看着,手的吮吸却没有隔离。
“喜欢、...。”
“下面也挺起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他拒绝得很轻,因此贝瓦尔德开始动手套弄起仍锁在裤中的凸出。提诺以极小的幅度开始颤抖的时候,他自己都为这颤抖结实地吓了一跳,但旋即便是习惯与忍受,他的心很快就适应了习惯与忍受。他挽出自己的一只手臂衔在嘴里,轻柔地咬着,好让自己能够有快活得发笑的余裕。拉开拉链的声音静悄悄的,有人在问:
“不喜欢吗?”
“喜欢、...。”
拉链重新合上了,提诺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衬衫已经透湿。他抬起手臂,看着浅浅橘红色的牙印像看着名贵的手表,这只手臂遮住了贝瓦尔德的脸,哪怕他在抬起身子。提诺只是冲着手兀自地噙着眼泪,然后偷笑了一阵,那浅橘红色却渐渐地从手上淡了。他正想追赶消退的牙印,却从手臂背后见着了光,圆柱状的夜灯稳稳当当地落在自己酸胀的胸口,贝瓦尔德看着自己了。
“接下来还要继续吗?”
他心里是急促地渴望着继续的,因此回应的语气已经不似往日般柔软,而是发涨、富有弹性。贝瓦尔德的手近了,一只手托起他的腰,于是他闭上眼睛,期待着另一只手落下。他等了有一会,不知另只手会伸向哪里,只要他能在腰际被托起之时,尽可能地忍受胸口的闷,这闷绝的拉链也一定终将被贝瓦尔德彻底地赤裸、彻底地公开的。他感觉有什么东西被拉开,腰在外部被一块坚硬的东西顶撞着,另一只手从他的腰际拉出了这坚硬的东西,像是被从沙发坐垫下抽出。提诺并不感到奇怪,现在他什么奇怪也没有,可那腰上是什么呢?
“喜欢吗?”
没有等待,也没有期待,他的腰渐渐贴着沙发坐垫了,黑暗中,属于他的拉链便被拉上了。提诺仍然紧闭着眼,为的是等到更多的拉链,更多的拉链被拉开。他听到塑料硬壳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打开。他的脸滚烫着,直到冰凉的手捧住自己的脸,拇指和食指拉开他闭着的眼皮。他只是顺从着,顺遂着,他期待地睁开眼睛,等待自己的圣诞礼物。
他睁开眼的时候,却看见一片鲜红。
“喜欢吗?”
贝瓦尔德的脸在崭新的塑料壳上变得不可辨认。
“想继续留在这吗?”
眼球凸出、尸体半边汹涌如柱的红流里,静默地垂成一线的脑回,像一条沮丧的蛆。
“还喜欢我吗?”
橘色的灯光把这具尸体照得光明磊落、不可侵犯。尸体的胸腔内结成了蛛网。
“哪怕我是杀人犯、一个杀人犯?”
贝瓦尔德在这张专辑的B面后面笑着,笑得光明磊落、不可侵犯。
“还喜欢吗?”
贝瓦尔德的声音在笑,笑声在无辜地、哀求着地颤抖着。
提诺逃跑了。
“还喜欢吗?”
艾斯兰这么问了。提诺把他从书桌前抱到床上、再帮艾斯兰批改起作业,不时拉动窗帘调整台灯的亮度,好让它和星光能够交融出一个既不过分奢靡,又不过分清冷的色泽来。提诺想起些什么来,又把艾斯兰从床上抱到书桌上。
“我应该睡在哪里?”艾斯兰有些恼火。
提诺一边思考着艾斯兰的发问,一边手中仍在展平自己将与艾斯兰共枕的床铺。他热起电熨斗往上贴紧,用热力好让这床单看起来能够齐整一些。但他无论怎样铺展,床褶都重新翻折回去,像一颗卷曲的螺旋,又像是一只床单的耳朵。他忽然感到一阵恶心,胃液从腹部翻涌上来,迸射而出的却是眼泪,直挺挺地落在床上,刚熨平的床单湿了,泪渐渐没入毛绒绒的床单里,只是总凝结出面上黏糊泛白的东西,他知道是刚刚的光线又没能调好,但他现在伸不出手去,仿佛定身在那滩乳白的泪之中,仿佛乳白色的眼泪黏在他的眼球之上,成为里头的一块眼白。他知道自己今晚为什么睡这床,是贝瓦尔德来了,他从壁炉旁的沙发又搬到这儿来,他要与瘫痪的学生共眠。学生的瘫痪由他而起,他或许此刻也正以自己的瘫痪报答学生。他回过头去,星光与二极管的灯光把书桌旁的艾斯兰衬得光明磊落,不可侵犯。
“你在害怕吗?”
提诺点了点头。
“...谢谢,提诺、老师..。这一年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
他示意提诺送他上床,向着提诺涓流般流淌的泪中,揩出一条平整的道来。
“好好休息,老师。”
他的双眼渐渐模糊。艾斯兰后来似乎还自言自语了很多,但不一会便开始翻动床头的书、一页页地在灯下照看着了。艾斯兰感到提诺的掌平放在自己的腹上,渐渐地又温热起来——这是提诺设计的康复训练的结果。他们或许都想起了父亲与壁炉,因而还微微留一点眼泪在枕上,他还想回上几句,表达自己有在倾听,只是耳朵却渐渐地被水声没过,在月光里静默成为了一滩乳白的泪。
“那之后,我便要连姐姐和你的��、...向贝瓦尔德讨回来。”
讨回什么呢?提诺轻声地对自己说,却不愿意睁开眼睛。
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却知道这里应该是艾斯兰的房间。迈过房间去,他便一定会见到贝瓦尔德。这房间对他来说很惬意,科勒夫妇向这个房间倾注了太多的爱意,当他抱着有轻微鼾意的艾斯兰、听取其中无数噩梦的梦话而沉沉入梦的时候,他渐渐地总觉得自己像是孩子一般。他伸出手去,攀上同床连为一体的书架。艾斯兰的桌边总是摆满了书。他从前总是静静地坐在班级的角落,在他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板书的时候,嬉闹的声音中似乎总是缺了现在对他来说太过熟悉的声音:同十岁的他一样怯懦、同十岁的他一样坚强、同十岁的他一样柔软的声音,在轻轻念诵着书架的书上晦涩的词句。
“我又带书过来了喔。”
在最开始进入这个家中的一个月里,叩响艾斯兰房门的总是这一句话,那会为提诺与他背包里的小说赚到一些难能可贵的善意的目光。提诺总是爱在教科书里夹上一本,当他从背包里将它连同半块黑面包拿出的时候,给同一个班上生物课的,外号“尖老头”的克里夫总是会同大家一起抛来怜悯的目光,仿佛他的姓氏就像进化论中的一个玩笑。《万奈莫宁》总该是写给有黑面包以外的食物享用的人才是,就连万奈莫宁本人也该是从大熊座那里得到种子以后,才渐渐开始吟唱他的诗歌的。他知道尖老头不会说,他一直想请人代课治疗咽炎。直到某天,尖老头环顾四周良久,才终于向他开口:
“请您替我代班上一星期的课吧。”
但艾斯兰却把《万奈莫宁》放在书架最触手可及的一端。他够了够那本书,就着窗边微弱的阳光看诗,像从前父亲用手指舔着书页,一边用舔过书页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头,在壁炉边为他念诵古老的诗歌一样。父亲不是诗人,但他慈爱的眼镜里似乎有诗人才能看见的世界。提诺看见艾斯兰在《万奈莫宁》一书上贴下的密密麻麻的书签,正要从胸中由衷地呼出舒服的气来,却发现床边早已空空如也。
他要迈过这房间去。他在门的这头,听见了外面不断地传来熟悉的呻吟。他捂住了嘴唇,眼泪几乎快夺眶而出。
“还喜欢吗?”
他的手心在出汗,门把却因打滑而无法转开。当他旋开门把夺门而出时,艾斯兰早已带着一身热汗倒在地板,还在喘着粗气。
“哎呀、...今天真是好睡啊,提诺。”
马西亚斯扶起艾斯兰的手腕。
“今天你起得格外地晚、我就事先先替你做了,阿冰每天要做的康复训练。”
“我不要再让你来做了...你这白痴、...。你是完全的傻瓜..。”
艾斯兰眼里还有泪。
“我不要...、...”
“看,提诺你看。阿冰他——”
提诺的沉默并不是绝无来由,而几乎是千钧一发了。马西亚斯是仔细地托着艾斯兰颤颤巍巍的双臂,他自以为自己的双臂足够可靠。但那可靠的双臂在艾斯兰站起的刹那腾了个空,接着他所希望向提诺展示的奇迹,便被提诺本人夺去。他伸伸五指,又抬头看看几乎怒不可遏的提诺。艾斯兰借提诺的手攀上沙发的浮岛,艰难响亮地呼吸着。
“您为什么、....!”
提诺想痛骂,却不知应痛骂什么。他张开嘴巴,口中率先回荡起的却是呻吟。
贝瓦尔德握着一把刀,刀在替他说话。
“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阿冰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马西亚斯是在帮他。”
刀在字与字的缝隙之间落下,贝瓦尔德在厨房的角落一字一句地把语言切开。
“提诺、今天你可以放假。”
戴着烤箱手套的西尔维娅说着,把一盘切好的生肉端进烤箱。提诺看见贝瓦尔德他低着头、他抬起头,鲜红的肉沫从刀尖挤到手指之上,被冲进水槽里。厨房的阳光现在已经好了不少,能看见北欧少有的阳光。案板上整整齐齐的肉排在这阳光下泛着漂亮的油光,贝瓦尔德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很满足似地把目光对上一旁的偷窥工作者。
“为什么、..”
提诺的问话声音很低。
“今天你起床要比以往都迟上不少、生病了吗?”西尔维娅脱下一对烤箱手套,把手贴着提诺的额轻轻地说。
“不、...”
“没关系,不用愧疚。”
西尔维娅帮他整了整毛衣的领子。
“我想...可能我们家真的离不开你。但你说的也对...总要让你做个决定,对吗?至少今天和明天,希望能够让你好好歇一歇。”
“我打算今天带你和阿冰出去转转。”马西亚斯借机用一个勾肩搭背略去了此前同提诺的剑拔弩张。“你平日里真的太累了。我从来不知道帮阿冰做康复训练是这么累的一件事!汗我都出来了!”
“因为你是傻瓜。”艾斯兰声嘶力竭。
“可你能站起来了,是吧!你们刚刚都看见了,阿冰站起来了!”
这热烈的呼喊声便把艾斯兰淹没在火红的沙发之中,由马西亚斯带头的掌声便响起来,在西尔维娅歇息的餐桌旁响起来,在贝瓦尔德仍在忙碌的厨房旁响起来。提诺的耳畔,竟也响起了来自他自己的掌声,他不知道自己的掌声从何而起,却不忍去看艾斯兰的表情,而是转头对上了贝瓦尔德。
“今天我有贝瓦尔德帮厨。他说想试试看,能否在晚饭做他拿手的肉丸。午饭,我们两个人随便吃点。”
丸子从贝瓦尔德的左手抛到右手、右手抛到左手。他仿佛极为专注、极为投入地炮制着干练的晚饭。西尔维娅在提诺的脸上落下一吻、又在马西亚斯的唇上落下一吻。她还想接着吻一吻艾斯兰,只是没能吻上,便帮他整了整领子,又折回原地,她疲惫的面容上总归是笑了。
“能在天黑前回来就好了。”
“您好、您好、...”
“您好!哟!——”
“你好!——”
“我们当家的!马西亚斯休假回来了!”
马西亚斯吹着口哨,麦当劳一楼餐厅里耸立起一呼百应的口哨与欢呼。
“还没呢、还没呢。”
马西亚斯满足地笑着,手却搭上一个餐巾上挂着鼻涕的孩子。那孩子正努力学着大人吹口哨的手指,把唾沫喷满了一整个餐盘,只是抬起头,马西亚斯的手便揉起他的脑袋。
“你真努力,不是吗?不过、用不着这么努力也可以。”
他举起孩子,孩子的母亲用双手屏住了呼吸,盖住了矫情的热泪。
“看呀——!这是努力的孩子!”马西亚斯高声朗笑,欢呼一浪高过一浪。
“我讨厌他们。”艾斯兰坐在轮椅上轻声地说,或许是声浪太强,好像没听到似的,提诺仍是点单。放下孩子以后马西亚斯呼唤所有人安心用餐,立刻便有人从服务前台行到艾斯兰坐着的餐桌旁,挨着轮椅换了张小桌,其后又询问起是否需要代切汉堡。
“他自己可以吃。”提诺礼貌性地笑道。
艾斯兰叹了一口气,让提诺把轮椅的把松开,双手滚着轮椅,寻找其他偏远的座位。
“我的服务生们要我留在这儿、他们离不开我。我不在的时候,这地方就开不下去、但总得有人休假,不是吗?我得陪你们,还有西尔维娅。”
马西亚斯找着新位置,便接着对提诺这么说,不时还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那远方的服务台终于没再看他,于是马西亚斯回过头来,边聊天边督促艾斯兰不要噎着。
“待会要去公园散散心吗?”他抚摸着艾斯兰的头。
“也不坏。”艾斯兰把头埋进大人们视线所不能触及的高桌的阴影下,提诺听到矮桌旁传来吸饮料的声音。
“我们去福洛格纳。”
等到提诺用手指把艾斯兰的发捋得柔软了,艾斯兰便用手推着轮椅的轮向前行去。马西亚斯锁上车,便同提诺一起缓步追着车辙。
不知是因为此时正是阳光的正午,天空才十分明亮刺眼,还是因为他不知道在这样灿烂的阳光下得做些什么才能称得上休闲,因此未向前方睁开更多的眼。艾斯兰的轮椅不停地向前方滚动着,他不知是否该把步子加快一些,与其说他在看护着艾斯兰与轮椅,不如说是艾斯兰在牵引着他进入公园深处。周围的人脚步虽缓,却从未停下正眼看过那轮椅一眼,只是略略向旁躲开、再躲开一些。于是有些拥挤的人流里,中央拉开的一方平坦,便像是为艾斯兰的轮椅所划开的道一样。提诺没有听见两侧高耸的人浪中窸窣的议论,只是向前行走。
“我们现在也像是一家三口,对吗?”马西亚斯忽然冲他笑。
提诺没有回答,这时他或许觉得自己和马西亚斯有些像摩西的子民。
圣诞前夕,渴望圣灵降临前的人们,都在正午时分踏上遍地的冰雪,前往福洛格纳的中心。这里的访客太多了,与挪威人印象中的市集相比而言都有些拥挤。杉松只在挪威的秋季死去,他们的枯枝上渐会伴行着冬日的纷雪涨成全新的行道树,它们全新的,纯白透晶的叶却是从地下抽枝起来,因那雪下的大时,极寒之地的雪便不像从天上恩赐,倒像从地上飘起一般。在终于停雪,却也仅有几日阳光的时节,公园的工人会把雕像的头顶、基底和纹路里堆积起来的雪同地上的积雪一般清理干净,只留下一道更深的痕迹。这是只有彻底的天寒地冻之中生出的人类,才可踏上足迹,去经行的地面。
提诺已经许久没有踏上过这样的地面,或许他也踏过,但从未仔细地行过脚下的路。他习惯照顾的是科勒家被壁炉烘烤的,从不积雪的地板,如今定睛细看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好似踏着柔软的布一般,脚步尽管因此飘然,却有了些实感。
“怎么样,怎么样!没来过吧?”马西亚斯口中呼出的白气几乎把提诺所能见的面容尽数遮挡,只从语气里可以看见他的笑。在他的印象之中,马西亚斯先生似乎永远只有微笑和大笑,好像昨夜哭泣的酒会从未发生过一般。
他来过这儿,尽管离科勒家有些远,但在他成为科勒家的用人之前,他便已拜访过这公园。路并不难走,却少了公园的气氛。马西亚斯揽住了提诺的肩膀。
“小孩们也都喜欢来这儿玩,那些雕塑的花纹对他们来说很新奇。”
“得把阿冰叫过来。他走得有些太远了。”提诺望着冰雪之上尽力滚动的轮椅。他在远处轻声呼唤,阿冰便停下来,向后伸着头等了一阵。白雪在他白雪般的发下,在他的额前闪光,因为推着轮椅,他的额上大汗淋漓。
“我们真的很像一家三口哇!”马西亚斯拍着提诺的脊梁。
“这话可别被西尔维娅小姐听到。”他却没有接着往下拒绝,马西亚斯便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齐步向前。
提诺帮阿冰揉了揉手臂,他们便接着向公园深处行去。积雪从赤裸的雕塑上被扫清,露出它们彻底自由的解放来。风雨淋洗的锈像在无数行道树之间昭彰着青与黑色的坦然,男人从雪与铜中解放的器官,有如路牌指示着通往喷水池还要深处的,更加雄伟的雕像,他们远远地望过去,那根柱子好像一只天地间巨大的灵。
“再往上走吧,我想看看那个。”艾斯兰头也没有回地说。
“阿冰今后会成为古斯塔夫·维格兰这样的艺术家吧。”马西亚斯说。
“他也很喜欢科学。因为阿冰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喜欢思考。”
“喔——当然,思想是很高贵的事情。正如卢梭所言:只有高贵的思想,没有高贵的血统。”
“您很擅长言谈,这点让我很羡慕。...刚刚,在餐厅里,您那号召力很是令人吃惊。”
“没什么、这没什么。一份工做久了,自然就会和身边的人混得熟,经理的工尤其如此。您不也一样吗?西尔维娅和贝瓦尔德都很喜欢您。”
“...不一样的。这个、...”
“我们家原本就没有找佣工的打算。如今佣工也叫保姆,还是有不少人喜欢雇保姆的,全职的、小时的;男的,女的。但是我们家一贯以为,在现在的挪威做这种事,那是贵族做派。可现在他们俩可舍不得你啦!只是他们俩不说。西尔维娅也不说,他们总是有些害羞的。”
“谢谢...请代我向西尔维娅小姐转达感谢。也谢谢您。”
“我也很舍不得你呀。”马西亚斯说。
“我还没有打算要走...我在犹豫着。我还有想弄明白的事情。”
“让我猜猜——是贝瓦尔德?”
马西亚斯把手臂向下垂下去,却只是冲着天空在自言自语,因此在话语里,他藏起了提诺突然糟糕的脸色。
“他同市教育局的人员也都认识,这事你应该听说了。重新给你安排一份教职,或者向原先那地方讨一份声明、推荐信什么的...当然不在话下。你还没找他通通关系吗?毕竟他也偶尔只来咱们家一次。他出身很高,可不像我。他姓乌克森谢纳?知道吧。名门之后,他爹是那有名的大提琴手,还是他们老家的议员,在挪威是提琴手,在他们老家是议员。乌克森谢纳家是世家。他处处都显着乌克森谢纳家的绅士做派。”
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努了努嘴巴,沉吟了会,突然笑起来。
“我戒了挺久的烟了,老这样!”他高高地把手扬起来,给了自己一嘴巴子,又自己行了几步踉跄,差点扑上在前方带路的轮椅,只是他的脚间交叉一拐,却巧妙地把身子拧回提诺身边,大口喘着粗气。提诺不知该对这超现实的花招露出怎样的表情。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笑,笑着笑着,看提诺不笑,他就不笑了。
“我抽烟的那阵喜欢像我的父亲一样抽烟,还喝酒。烟已经戒了,酒还是没戒。他抽烟的时候不打人,喝酒的时候打人。他搞黑金属,我和他也一起搞黑金属,因为搞的时候他不打我,还有烟可以抽,有酒可以喝。我们的乐队那时很出名。”
喷泉的水声清冽地冲刷在石的阶石之上。艾斯兰的轮椅在前往“生死柱”的阶梯前停下。马西亚斯把手插到大衣的口袋里,让旁人以为他的假烟已经抽完了。
“阿冰,想上去吗?”
“想。”艾斯兰说。
“提诺,搭把手。”
提诺抱着艾斯兰,马西亚斯抬着轮椅,艾斯兰在两个人的中间脊梁绷紧。他们经过36座扭曲成不同形状的人体,又经过回头,向这蠕动着的三人慕道会报以怜悯目光的无穷的路人。正如马西亚斯所言,冬至日也刚刚过去不久。从他们来时这天还蒙蒙亮着,不一会便渐渐黑了,星辰都渐渐在他们的头顶上显示出来,好像是一夜之间,石头上色彩便从此转暗了。这在北欧总是非常很常见的,周围的人渐渐离开,没有人想要在黑天的时候,在公园里惬意去。他们一级一级地行上台阶去,彼此之间似有一种微妙的、沉静的默契。
“我听说您是丹麦人?”
提诺发问。
“丹麦和挪威离的也不远。”
他们经过人们的雕像,与看雕像的人们。“生死之柱”渐渐地近了,那是挺高的一根石柱,不算太高,但是的确挺高。他们在中间的坪停了停,提诺摇了摇自己的手臂,马西亚斯则是捋了捋自己的手指,艾斯兰则没有动,只是撅着腰,等着下一次再被抱起。
“我听说,我也不是挪威人。”
艾斯兰发问。
“怎么这个时候提起这个?你是我和西尔维娅领养的。因为不知道你的名字,把你起作你的故乡的名字。”
“生死之柱”渐渐又近了,那上头已经可以看见是人了。或许是因为它挺高,略略往上些的积雪便没有清理干净,落在人和人之间的缝隙里,使得“生死之柱”高贵而坚挺的柱头染上了一丝圣洁的雪白。这根柱据说是链接天国的柱子,在靠近天国的这根柱子上,当然应该沾点天国的白雪,只是因为柱子的顶端是平坦无比的,因而在刚被太阳晒过的时候,最该圣洁的地方反而是全无雪白,一览无余的平地,上头有化雪后水的黑色染痕,同柱子的最下端,最为平坦的那层一样。底层刚化雪还没多久,因此底层罗马式的柱黑得笃实,坚定,隐忍,但也没有黑得太多,只浅浅的一层,便过渡到了石头了。中间就是人。这根雄伟的,博大的,挺拔的,高尚的柱上,全都是人。
人。人。人。人。人。
艾斯兰努了努嘴。
“阿冰,往上走过来的路也有讲究。”马西亚斯笑着说,“每条路上的雕像不一样。有儿童的路、有青年的路、有老年的路——”
“那我们走上来的是哪条?”
“最后一座就是这里。看这根柱子,人和人都拼起来。”
“拼得起来?”
“像一组上升的旋律!”
马西亚斯恐怕觉得自己这比喻很好、很巧妙,很能给艾斯兰以艺术的灵感。吸饱了艺术的灵感的艾斯兰接着努了努嘴巴,好像吸了漫长的一口气。
“贝瓦尔德,就在这里杀了你的父亲。”
马西亚斯的眼角开始渐渐发黑,艾斯兰的眼角却渐渐泛红,红和黑都交成一块了、拧成一团了,在空气里擦出火花了。在维格兰静默的雕像群之中,儿童在苦劳、壮年在天真、青年在震悚、老人,只有老人在柱下独自死去。
马西亚斯恐怕是在老人枯瘦的尸体前坐了很久。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梦里见过。”
马西亚斯在老人枯瘦的尸体前坐了很久,才开始说:老人枯瘦的尸体生前是无恶不作的,老人枯瘦的尸体是该死的。尸体所到的地方,有一座基督教堂就烧一座基督教堂,有一杯基督徒的血,便饮一杯基督徒的血,他儿子的母亲便在他的酒杯,头盖骨便是他的酒杯。尸体用人肉的乐器唱世界上最邪恶的音乐,他很会唱,嗓子的声不光是金属的,还是黑的,不是被烟和酒腌的、是被血染黑的。尸体喝了血以后就醉了,醉了就打儿子、儿子迎醉长大,渐有了一身气力,尸体打他不过了,便朝他施以邪恶的萨满巫术。儿子看见自己巫术的眼中有马、有巨人、神、精灵和矮人,在烟尘之中迈出脚步,尽数从黄昏之下向他奔来,为首的独眼神明,唤名做伟大的奥丁。
马西亚斯说:尸体的儿子首肯了他的血脉,让连着同他前来的两个男孩儿也这么做、矮个儿点的男孩儿是个假声男高音,尸体让他替自己唱了歌;高个儿点的男孩则是提琴手的名门之后,老人让他弹贝斯和拉提琴,儿子则只打鼓。尸体只有两只手,俩手最多弹吉他与键盘,但加上两个男孩儿和儿子,就是八只手。奥丁骑着的马,脚也是,而他们四人拼在一起却绝不像马,而像蜘蛛,因为为首的那颗头并不是骏马的头。蜘蛛在大地上爬行、蜘蛛在教堂前爬行,有一座基督教堂就烧一座基督教堂,有一杯基督徒的血,便饮一杯基督徒的血。蜘蛛除了腿以外就是头,老人有了腿,就接上了老人的头,不仅有头,且绝只有他一个人的头,其余三人绝不可出头。尸体说:“成了。”第一张专辑就出来了。
“贝瓦尔德出了头。”
马西亚斯说:矮个儿的男孩儿渐渐长成了女人,假声男高音却没有渐渐长成花腔女高音。马西亚斯接着说,乐队的嗓子没了,尸体的嗓子里头却已经全是烟酒。贝瓦尔德听得分明,尸体最后说的话是:“得把他变成女人。”那之后他不再说话,嗓子里的烟会烫死蜘蛛、嗓子里的酒会淹死蜘蛛,但是嗓子里有女人就不一样,几亿的蜘蛛全都可以浸泡在乳色的大海里,从中再生出几亿亿的新的蜘蛛,所以他不再说话,只是动手。在维格兰公园平坦深厚的石阶上,枪与玫瑰没有打算隐藏。
“贝瓦尔德也会用枪。”
提诺在听着,眼前却不是一把枪,而是一只蛆,从脑回那里垂下来,在沮丧着,尸体的胸腔里,结成了蛛网。马西亚斯说:他不知道贝瓦尔德是怎么学会用枪的,就像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维格兰公园的柱下、他们三个是怎样离开了马西亚斯的父亲的,又是怎样长成新的男人、女人和男人的。他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得很大,很大。女人现在是马西亚斯的妻子,贝瓦尔德现在是马西亚斯的朋友。
“可是,一切都过去了。”
马西亚斯只是冲着艾斯兰笑,把他的头发揉成一团,又把他的头发根根捋顺。
“贝瓦尔德是杀人犯,但那又怎样?我父亲是个人渣,他早就该死了。正义永远不会杀死善良的人。对吧?我感激贝瓦尔德,他为了西尔维娅把自己弄疯了;我希望西尔维娅能幸福,这愿望也是他的愿望。”
“就连贝瓦尔德现在的疯病...也渐渐好转很多了。”
提诺离轮椅上的艾斯兰和马西亚斯实则很远,因此他的喃喃自语只是飘在空中。他只是不时点头。
“日子是在不断变好的。”
没有人说着这句话,他却在马西亚斯的话与话之间听见了这句,眼前渐渐起了一层水雾,这是欣喜与快活的水雾。他此前从没有把世界看得这么清晰,这么分明。他看见了“生命之柱”诞生的过程,在大地的震颤与轰鸣之下,人与人首尾相接,彼此咬合,膝盖与膝盖交叉在一起,人便向上攀登,通往天国的大门敞开着。那柱的顶端是谁?
对,应该是贝瓦尔德。贝瓦尔德·乌克森谢纳。他是名门之后,他是暗黑的、悲怆的英雄,他应该要是从伊尔马塔的腹中生出,再高高地立在大海之中的石柱之上。他曾经是乐手,万奈莫宁也是乐师;他现在是诗人,万奈莫宁也是诗人,提诺的姓氏在闪光。火炉旁抚摸着提诺的头的、慈爱而严苛的父亲有了形状,他就是父亲。在马西亚斯与西尔维娅需要他的手艺与力量的时候,他必然在铜船上归来。从铜船上归来,从墨西哥的东海岸归来,从阿瓦隆归来,从弥赛亚归来,人、人、人、人、人,一切都将归来。他赢了,他终��会是赢的!黑暗没有战胜他,光明却呼住了他!他赢了!提诺·维那莫依宁的眼中的雾气渐渐有了形状,喜悦和激动的眼泪重新袭上他的心头,他能原谅,他能宽恕,他想回去!他想回答!他能留下!
“还喜欢吗?”
“还喜欢、比从前还要喜欢。”
艾斯兰,你在哭吗?你和我一样在哭吗?
马西亚斯轻轻地抹掉眼角的眼泪。艾斯兰从轮椅之上,向提诺转过头去。那只是孩子,只是孩子而已。艾斯兰努了努嘴巴,好像刚刚抽干了一根烟。
“我看见过。我看见过贝瓦尔德。他不是英雄。”
“因为他做了和你父亲一样的事情。他玷污了我的姐姐。”
你胡说。
你骗人。
你什么时候见到的?!
“在梦里。我见到了。”
你这撒谎精。
你这爱说谎的孩子。
“但是不一样。在我还能走的时候。我也见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要骗人?
“节日的每一次。”他仔细地低下头想了想。“几乎是每一次。”
“艾斯兰!”马西亚斯是抢先一步揪住了艾斯兰的领子。他齐整的领子,现在被揪得出水。艾斯兰总是汗涔涔的,额头在汗的瀑布之中发着亮光。马西亚斯的手在颤抖,因为艾斯兰低着头,他低着头,眼睛闭了起来。艾斯兰紧闭着的眼睛前忽明忽暗地闪光,不停地闪着光。马西亚斯用拇指抹掉他眼角的泪,才发现艾斯兰也在发抖。当他的眼从发下暴露出来的时候,忽然他哭了。
“我想救你们、让我救你们吧...”
他伸出双臂抱住马西亚斯的头,艾斯兰的肺与他仅有的半身痉挛着,呼吸之中起来像冰冷黏着的雪粒在鞋与地缝之间摩擦。马西亚斯的眼神终于柔软了下来。提诺手里拿着刀、拿着枪了,就像贝瓦尔德拿着刀,拿着枪了。提诺看向自己的掌心,枪与刀都勒出柱的形状。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
马西亚斯没有再说话,艾斯兰却拼命地点着头。
“现在,我们回去吧,好吗?”
马西亚斯现在半跪着,双手掌心里捧着艾斯兰颤抖的泪和脸。他轻声允诺了好一阵,发现艾斯兰只是点头,从开始哭起便没有再说话。他抬头望去,满天的星辰下,提诺的眼泪轻轻打在艾斯兰的头发上。
他们仨都哭过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生命之柱”在哭泣的大地上矗立。
天已经黑了,今天的黑是特别的。如果平安夜的夜晚以黑夜的长度来丈量恩赐幸福的厚度的话,至少挪威人应该要是世上为数不多的、在世界的平安夜里最为幸福的居民。他们开车路过一角的平安夜。他们经过中央车站,从奥斯陆前往卑尔根的火车铁路会穿过南部那些被春风滋润的挪威森林,逐步爬升至美丽的哈当厄尔高原,常年飘雪四季如冬的芬瑟,接着穿过沃斯周边一众秋色无边的田园村庄,最后到达时常飘雨的卑尔根。至少他们中应该没有人去过卑尔根,因此从来只在平安夜继续向前。他们路过卡尔·约翰大街,从公交巴士下站的街口城墙上会倒映着锡箔的雪花,漫长如蟒的圣诞彩灯把楼和楼之间的人流拉近拉满,在逐渐上升的街道两旁是次列间错排开的国旗与市旗,还有挪威国王的王宫,和挂满彩灯的树木。孩子们在议会大厦与国家剧院中的溜冰场上驰骋,比昂斯滕·比昂松和亨利克·易卜生在冰面上注视着圣诞夜空下的一切:易卜生把手背过身后,看着冰面下的裂痕;比昂松则把手插在裤兜,高高地昂起头,看着冰面上满地玩耍的孩子们。
“今后会有机会重新来这里玩的。”马西亚斯对后座的艾斯兰说。
他停了车,今天是马西亚斯第一次在按下门铃前犹豫,在终于想起有钥匙之前,提诺已经率先把钥匙插进了门孔之中。他回头去把在轮椅上等待许久的艾斯兰抱回家门口。迎着敞开的门,他和艾斯兰都看见了全新的装置。
“这是贝瓦尔德为阿冰准备的圣诞礼物。”
提诺已经换完了鞋子,他转头去看壁炉烧火的情况,才忽然发现那并不是真正的壁炉,而是电壁炉。这电壁炉看上去使用已经颇有些年头了。他看见贝瓦尔德仍勤快地在簿上抄写些什么,只是在西尔维娅提到他的时候,才把笔插进口袋之中,转过身来。
“这是之前找市医院订做的截瘫步行器。”贝瓦尔德说。“试试看。”
他站起身来,伸出双臂想让马西亚斯把艾斯兰交给他。他的手牵起艾斯兰的双臂,感觉手里握着的触感是颤抖的。他不知是马西亚斯的手臂在发抖,还是艾斯兰在发抖。
“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圣诞故事,况且这个也塞不进袜子里。现在试试看。”
他缩回一只手扶了扶眼镜,不知是被马西亚斯盯着了,还是眼镜的角度不太对。直到他摸起耳畔的一根深沟,才吁出一口气。
“现在不要。”艾斯兰的声音轻得像哀求。提诺转过身来把艾斯兰接去房间,又折回抱起步行器。
“我先放回他的房间去。”提诺像在和步行器说话。
“西尔维娅,您现在有空吗?”马西亚斯脱下外套,牵起西尔维娅的手。她的手上还戴着烤箱手套。马西亚斯尽可能轻地替她脱掉手套,好似戴上戒指一般柔和,西尔维娅没有出言反驳,也没有迟疑,她便随着马西亚斯向着房间走去。两边的房门都已经关上,贝瓦尔德拾起眼镜来。
这是平安夜最长的一段沉默,沉默得就像之前经行过的所有年岁一样。在贝瓦尔德的笔记上,不曾记述过的这首诗,此刻却非常应景,它们从四面八方响起,却又像来自天空的正中央。这是来自圣夜下,窗外边,每家每户的在沉默之中为祝福念诵的祈祷文,这是一首以色列人摩西的诗歌: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阿、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
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
人们在节日里默念这首祷文。在挪威人的节日中,昨天叫做小平安夜,今天则是大平安夜,今天要比昨天的晚餐吃得更加丰盛,正如今年要比去年的晚餐吃得更加丰盛。艾斯兰坐在餐桌的窄边,宽边上则两侧分开,提诺与贝瓦尔德坐在一侧,西尔维娅与马西亚斯坐在另一侧,靠南的一边则尽数交给了窗,与窗外尽情绚烂的烟火,如果从窗外看去,还能发现窗外彩色的圣诞树。没有人知道今夜是如何到来、如何来到的,就像没有人知道这些菜肴是如何仅仅凭着两个人的手做出来的。他们动刀子、他们动叉子,三文鱼腹,黑面包还有香肠;他们倒杯子,他们倒盘子,肉丸,鱼子还有越橘酱;他们找乐子,他们动嘴皮子,羊排,猪五花还有熏羊头。
马西亚斯在那边举起酒杯:
“我们敬贝瓦尔德一杯!”
他们高高举起酒杯,马西亚斯爽快地一饮而尽。
“我们敬提诺一杯!”
提诺把酒杯举起,马西亚斯又爽快地一饮而尽。
“来,阿冰,你也来。”
艾斯兰说他喝果汁也喝不下了。于是只有马西亚斯一饮而尽。
“西尔维娅,来、来、来...”
敬西尔维娅的那一杯的时候,马西亚斯喝到一半的时候,便醉倒了,睡着了。于是接着,他们不再动刀子、动叉子、不再倒杯子、倒盘子,连嘴皮子和乐子他们也稀微了,于是人们散了,灯也关了,艾斯兰与贝瓦尔德散了,客厅与餐厅、走廊与房门、厕所与厨房,已经尽数地交付给绝对平安,绝对无憾的夜了。
没有人在等这个夜来临,也没有人在等,外面的人没有等,里面的人也没有等。奥斯陆的所有都收敛起了他们可能发出的光,卡尔·约翰大街变暗了,市政大厅变暗了,国家剧院变暗了,建筑与建筑之间捆绑起来的圣诞彩灯变暗了,孩子们玩耍的溜冰场也变暗了,冰面上没有比昂斯滕·比昂松,冰面下也没有亨利克·易卜生了。中央车站变暗了,春风吹过的挪威森林变暗了,美丽的哈当厄尔高原变暗了,飘雪如冬的芬瑟变暗了,秋色无边的田园村庄变暗了,飘雨的卑尔根也变暗,且暗得还要往远又更远处了。福洛格纳、维格兰雕像公园正中央,人与人之间用肢体堆砌的,从地表通往天国的台阶没有亮起来,地表和天国并不打算显示它们;就连肢体与肢体之间,微末的雪也没有再亮起来,它们是心怀感激地接受了黑暗的。黑暗在沉没,夜在沉默,只有说要有光,它们才会重新亮起来,像这照耀地球的日光一样。光没有来,它们也不来,光说要走,它们也不会停留,光会消失,但不会隔绝,黑夜长存,但绝不永存,一切没有等待黑夜,它们只是在享受黑夜,一切在等待光,连黑夜也在等待光。
光来了。
贝瓦尔德赤裸着。
西尔维娅赤裸着。
马西亚斯赤裸着。
提诺看着。
尸体也看着。
西尔维娅把尸体端正地摆放在自己面前。
“贝瓦尔德不是杀人犯。他谁也没杀。”
电子的炉火在机械地燃烧,烧得各外通红。在马西亚斯还没有挥出拳头,贝瓦尔德也没结结实实地挨下那一记拳头的时候,提诺在他见到贝瓦尔德的那个沙发上见到了西尔维娅。她把尸体从专辑唱片里搬出来,让提诺用食指和中指去仔细触摸。在提诺没能摸到手的时候,西尔维娅从唱片的B面又抽出一张纸来,把它细细地展平了。那上面全是字。
“这是遗书。至于封面上,那是他自己来的。不一会就死了。”
“他从前很亢奋...毕竟也喝酒。马西亚斯现在会喝酒,也都是和他学的。但是连他也没有杀过人,更不要说他妻子。是有一天她起床上厕所,在厕所里滑了一跤,死了。然后他就开始喝酒,马西亚斯就是和他学的。喝酒以后就是抽烟。
他的烟抽多了,咳嗽的时候的声音被人听得像黑金属,于是让那时饿得快死的马西亚斯帮他找人来听。有人爱听,贝瓦尔德就爱听。他家里人不让他听这个,所以贝瓦尔德愿意花钱。他也有钱可以花。
他的烟抽得越来越多了,歌也唱得越来越好了。但是除了贝瓦尔德没有人在听。基督教堂也不是他烧的,但是总有人在烧,于是渐渐地就是他烧的,人也就渐渐是他杀的了。”
西尔维娅把照片贴在胸口。
“这都是他摸着我的胸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我的假胸像他死掉的妻子,摸起来比真的还要更真。我知道他不是想和我说话,他是想和胸说话,说着说着,他就忽然哭了,说毕竟不是真的。他那以后就常哭。
他溜到维格兰雕像公园的半夜,是他带着我的。对着我的胸,想让它告诉贝瓦尔德点事情。他不在乎马西亚斯,也不是在乎贝瓦尔德。他应该是在乎贝瓦尔德的钱。
假胸不可能告诉贝瓦尔德这些事情,但是马西亚斯知道了。召去辨认尸体的时候,先一步赶到的却还是贝瓦尔德。
唯一说对的是,贝瓦尔德真的拿了枪,是他自杀用的那一把。他的脸上都是鼻涕和眼泪。”
贝瓦尔德的脸上全都是鼻涕和眼泪。他的眼镜已经碎了,却不是在脸上碎的,是浴室的镜子挨着他的背先碎了,在灯暖被飞来的碎片击碎的时候,他滑了一跤,眼镜就是在那时被他用膝盖跪碎的。他插着全背的玻璃,但仍挺立着,全部流着血,在铁青的脸上爬行。他用这双膝盖爬出浴室,马西亚斯用那双脚退出浴室。
“如果不是因为枪里面只有一发对准了颈动脉的子弹,也在他死的时候被用光了的话,这张封面上的脸还会那么完整、血和脑浆还会只从这一个地方流出来吗?”
贝瓦尔德的全身现在都是血,他伸出手,往脑门一直抹到脖子,让玻璃的碎渣割破了自己的手掌。他站起来,马西亚斯往后退了一两步,他一直往亮着灯的走廊伸出手掌去,又伸回自己的面颊,瞪着掌心,好像自己的眼球理应更多地瞪出一点血,应该喷到手掌心里,没过每一缕掌纹似的,但眼球终究没有流出血来,什么血也没有。
“贝瓦尔德那时在咆哮。他已经被按到了地下,还在咆哮。”
贝瓦尔德在咆哮。
“我是...”
他伸出被割破的手掌,使劲地把已经脱落的玻璃摁进自己的脸颊,头发在四处飞溅,他用膝盖在满是玻璃的背上行走着,每一下的膝盖没能笃出全然的声响,他便用拳头砸进地面,木屑和油的声音在断裂。他的咆哮没有单词也没有语法,只是用黑色的声音在咆哮,咆哮的临终,他终于咆哮出了一句话。
“我是一个、维京人——!”
马西亚斯的怒火变成了害怕,两行热泪流到唇角。当它干裂的唇纹被泪水浸润以后,那满是利牙的上下颚便猛地从中间裂开去,他的双唇便自此皲裂,从里头渗出全然的,令人羡慕的血来。
“马西亚斯那时候在我的旁边。他很害怕,他那时候甚至哭了,这是他后来对我说的。但是哭了以后,他反而变得好战起来了,他并不是一个好战的人,这也是他后来对我说的。他对我说很多,包括后来他说他忽然喜欢我,他说他想给我幸福,他说他想要个孩子。这些都是真的。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忽然从我的手里挣脱去了,他去抢到了贝瓦尔德用来射他爸爸的那把枪。”
马西亚斯掐住了贝瓦尔德的脖子,他的血混着贝瓦尔德的血,在他的双手里握着。
“但那只是一把空枪而已,被按在地上的,紧闭着双眼的贝瓦尔德没有听到,紧闭着双眼的马西亚斯也没有听到。”
“因为枪只响了一声,只有我听到了。”
西尔维娅从碎裂的镜子里走出来了。她的眼睛睁着,胸前赤裸着,两颗假胸在那之后荡不起任何波纹。
“枪响的时候,他在我怀里,还摸着我的胸。后来,贝瓦尔德每次也都是在浴室,一边接吻一边摸我的胸。马西亚斯也早就知道,他只是不说。他不说的时候,我也让他在我的胸里。贝瓦尔德只是同我接吻,马西亚斯只是哭泣。没有人杀过人,也没有人玷污过我。”
提诺看着西尔维娅,看着她的胸。
赤裸着的西尔维娅,赤裸着她的胸。她说:
“你们要像维京人一样决斗吗?”
她说完以后,转身便从容地在他们眼前离开,屁股和胸部都在风中赤裸着。只是因为太暗了,或许因为彼时她自己的血已经糊住了她的眼睛,她看不见往前的路,在跨脚往卧室,去取她所说的“给维京战士的斧子与盾”的时候,跌了一跤,便自此昏在了地上。一具裸的女人,四处都光滑的女人,横亘在了贝瓦尔德和马西亚斯之间。他们的血早就在风里和热里干了。
提诺听到西尔维娅的最后一句话,却不是这个。他听到的西尔维娅说的最后的话现在还分明。
“贝瓦尔德也和你一样喜欢你。你们是互相喜欢的。”
西尔维娅低垂着头,疲惫地微笑,询问着。
“可是你真的要离开吗?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吗?”
他看见贝瓦尔德和马西亚斯去探西尔维娅的呼吸,去探脉搏,去摸体温。他应该是回到了艾斯兰的卧室,那个有星光与灯光、还有《万奈莫宁》的房间。他帮艾斯兰的身子翻了面,在星光与灯光下,艾斯兰朝上的脸尽是无穷的水渍,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提诺应该是太累了,所以倒头便在床上安眠而去。
他听见睡梦之中,星光和灯光下的艾斯兰说:
“快逃跑。”
“那你怎么办?”
他努力在梦里去奔向光明的前方,门打开了一扇一扇一扇一扇一扇又一扇,在扇与扇的最后,他睁开了眼睛,艾斯兰不见了。
他在打开的门背后,看见了整洁如新的家。浴室只是空了,却没有镜子的碎片也没有血迹。走廊上没有血迹,没有打斗也没有晕过去的西尔维娅。马西亚斯在笑着挽着艾斯兰的肩膀,贝瓦尔德则戴上了全新的眼镜,替他的腿和他的腰穿上全新的截瘫行走器。艾斯兰平举着双臂,在马西亚斯放了手的时候,艾斯兰结结实实地站在了家的正中央。
窗外的挪威人的欢呼声在庆贺圣诞。今天是圣诞节。
“成了。”马西亚斯笑着说。
“成了。”贝瓦尔德扶着眼镜说。
艾斯兰回过头来,提诺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里见了提诺。
“我已经逃不了了。”
贝瓦尔德搀着艾斯兰的左手,马西亚斯扶着艾斯兰的右手,他们打开门,先跨出一步去,静静地等待艾斯兰用自己全新的双腿往前迈去。艾斯兰渐渐把头朝提诺的方向,渐渐地拧回门的方向,他也向着门外头去了,双脚最终落在了门槛外面。
“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西尔维娅。她摔伤了。”
提诺在门外仿佛看见西尔维娅,她轻声问询着:
“可是你真的要离开吗?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吗?”
西尔维娅站在他们之中,刚好是四个人,八只手。他一时分不清这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说的话,但是他们全都向着提诺挥手道别。他们挥手道别,就像第一次挥手见面一样,门便从此关上了,房间的屋子里响满了关门的声音。
4 notes
·
View notes
Text
ずいぶんと昔の話です。
田舎にある地方大学の軽音楽部に、あるバンド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名を「酸駄馬阿土(サンダーバード)」と言いました。
お世辞にも上手いとは言えない、本当にヘタなバンドでした。
演奏ジャンルは、バラバラ。
ポップス、ハードロック(メタルなんて言葉がまだない時代です)、歌謡曲、ニューミュージック…。
オリジナル曲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だから、メジャーデビューなんて全く考えていない、楽しければいいというバンドでした。
だから、演奏曲は徹底してノリのいい曲。
この曲は、こんなにノれるんだという絶妙な選曲。
このバンドのベストアルバムを作ったら、それは意外なくらい楽しくなると今でも思います。でも、それはオリジナルのバンドや歌い手ではダメなのです。
このヘタクソなメンバーの演奏でなければ。
リズムパートは、ドラムは微妙に不正確、途中で速くなったり遅くなったり、ベースはアクセント位置が一定せず、音量も上がったり下がったり。
リズムギターは、コードを押さえるのに必死で顔がひきつり気味。腕の振りは、まるでフォークギター。ストラトキャスターなのにズンチャカ、ズンチャカ聞こえて来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した。
リードギターは、あがり症とかで、演奏ステージに上がる前に、いつもベロンベロンの手前くらいまで酔っていました。だから、せっかくのソロパートでも、押さえているフレットが半音ズレていても気づかず、キメ顔での演奏に聴衆は大爆笑でした。今剛やマイケルシェンカーを神と崇める彼の実力は、大学の軽音楽部中でも一二位ほどの腕前だったとか。まともな演奏は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ちなみに、一位の人は、卒業後プロのスタジオミュージシャンになったそうです)
ボーカルは、これまた単純にヘタなんです。ただ声量があるので妙な説得力。
これが女性アイドルなどの歌を歌うのですから、そのミスマッチは見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くらい破壊力がありました。
この誰一人としてまともなミュージシャン志向の者が居ないのに、聞いていると実に楽しいのです。バンドメンバーはとても仲が良く、曲間の掛け合いすら「芸」でした。
このメンバー中に、音楽才能が少しでもありそうなのは2人だけ。
よくこれでバンド組もうという気になったな、という感じです。
リーダー(リードギター)に、経緯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ーーーー
みんなで酒を飲んでいた時に、僕が「ハードロックやりたい!君達もギターを買え!」と言ったら、「じゃあやるかぁ」と決まった。でも、死ぬほどヘタだったので、「辞める!解散する!」と言ったら、「いいよ、でも一緒に酒も飲まないよ」と脅されたんだ。で、プロを目指すのを諦め、酒を取った。ーーーー
このようなバンドですから神話はありませんが、エピソードはいくつか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1)初ステージで上がってしまったドラムが、やたら速いテンポカウントで叩き始めた。
興奮状態のドラムはさらにテンポアップし、皆が必死でそのテンポについて行こうと演奏していたが、ついにギターが「こんなん出来るかぁ!」と演奏を途中で止めた。
(2)ステージの演奏テープを部室で皆で聴いていたら、先輩バンドの人が、「お前ら、すごいなぁ、俺ら自分達の演奏聞き返す勇気はないわ」と感心していた(呆れていた)。
(3)結成間もない頃はレパートリーが少なく、学祭時のライブでは3曲くらいしか持ち歌がなかった。教室をライブ会場としていたが、観客は他の人気イベントに取られ5人くらい。夜の部でも観客の入りは悪く、先輩/同期のバンドはそこそこ聴衆が来てくれるのに、自分達のバンド演奏時は仲間内の数人ばかりだった。3曲しかないので、ステージもすぐ終わってしまい、やることもなく座っていたら、先輩(院生)バンドのちょっと厳しい先輩が、「音出してないと、余計誰も来ないだろ!1番下のバンドがやれッ!」と至極当然の叱咤。「でも、うちら3曲しかないんですよ」と言うと、「いいからやれッ」。仕方なくその日何度か目の演奏を繰り返す事になった。終わったら「繰り返せッ」。また、3曲演奏。「お前らの演奏、ダメダメだけど『危険な二人(沢田研二)』だけはイイ!それだけ繰り返せ!」。
それから、その曲だけを演奏し歌い繰り返す。夜も更けて、他教室のイベントも終わり、行くところがなくなった学祭訪問者や学生たちは、大教室から流れてくる「危険な二人」の爆音に惹かれて、一人二人とライブ会場に集まってきた。他のバンドはもう飲みに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で、演奏しているのは「サンダーバード」のみ、会場を盛り上げ踊ってるのは先輩の院生バンドの面々。この後、どんどん人が集まってきて、会場は50人以上、演奏曲目は「危険な二人」のみを延々と繰り返す。何回繰り返しても止めさせてもらえない。イントロのリードギターが始まると、大歓声。ジャジャーンと終わっても、アンコール・コール。さすがにメンバーも他の曲をやりますか?と観客に聞くと、「危険な二人」でいいと言う。なん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トランス状態の中、カラオケもない時代、マイクで歌いたい人が多いので、ボーカルのマイクを奪って歌い出す。先輩が「マイクを死守しろ!」「わかりました!」と妙な戦いも起き始め、結局ユニゾンで大合唱。21時ころになり、大学外まで響く爆音に、学外の酔った社会人兄ちゃんたちも参入。さらにマイク争いが加熱。23時頃、皆声が枯れ出なくなってもまだ歌い続ける。さすがにもう無理と「ラスト!」「ウォー」との歓声の中、歌い終わって、メンバー、観客共にへたり込む。水代わりにウィスキーの水割りをガブガブ飲みながらの4時間余りの熱唱、踊り、歓声。終わった後、街の兄ちゃんたちが、「いやー、面白かった。これで酒飲め」と三千円くれた。最後まで踊って盛り上げてくれた院生バンドの先輩達が、「良かった!お前たち!演奏はサイテーだが、サイコーだ」と抱きしめてくれた。
危険な二人の演奏回数は、30回を軽く超えたらしい。
(4)ピッキングが強いので、リードギターは演奏中によく���を切った。こうなると他のメンバーは弦を交換し終わるまで何もすることがない。あまりに間が空きすぎてバツが悪いので、ボーカルが小噺を語った。非常に受けたので、弦が切れると、最近の面白いこと、創作ショートなどを披露するようになり、さらにこれが評判を呼び、観客は弦が切れるのを期待して待つ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さらに、幕間にコントっぽい動きも取り入れ始めたので、近隣短大では、コミックバンドと思われていた。「ぼくたちはドリフじゃない」と言っても、「あの話やってー」と短大生から声がかかるところまで行ってしまった。
(5)4年次には、とにかく曲と曲の間の語りが面白いと言う事で、離れた別学部の軽音楽部有力バンドメンバーまで学祭に見にくるようになった。先の一位の人が加入していた、この有力バンドは本当に上手かったそうだ。このギタリストとボーカルペアが見に来た。サンダーバードの演奏を聞いて(見て)、大笑いし感心して帰っていった。年も明け、この有力バンドは、卒業記念公演を県庁所在地のライブハウスを借り切って行った。すでに結構なファンも付いていたと言う。親交が深かったサンダーバードのリーダーも招待され見に行った。いつも淡々と静かにハイテクニックな演奏をする、それはそれはリーダーが理想とするバンドであったそうだ。しかし、この時の卒業公演は違った。一位のギタリストが、曲間につまらんダジャレとか小咄を入れたとのこと。いつもと違う風情の、お気に入りバンドの偏向に観客も戸惑いがち。サンダーバードのリーダーを一番驚かせたのは、ステージ上で「これは知り合いのバンドから聞いた話なんですが…」と、サンダーバードのネタをやった事だそうだ。ステージが終わり、楽屋に行くと、「面白かった?どう?」と以前とはまるで違うノリ。「どうした?」と聞くと、「やっぱり音楽は面白くなくちゃ!」とのこと。サンダーバードのリーダーは、戻ってメンバーに「僕たちは、日本の宝となる有望なギタリストを壊しちゃ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と語リ、メンバーは「それは、うちらの勲章だね」と笑った。
サンダーバードは5人が基本メンバーで、ドラム、ベース、キーボード、サイドギター、リードギター。特定の曲を演る時だけ客員メンバーとして外部の1名がボーカルを取っていました。ボーカルは、ベースかキーボードの人。ただし、歌いながら演奏するほどの技量はないので、ボーカルの時は楽器を交代したりキーボードを抜いたりしていました。
5人中、4人が4年で卒業。一人が院に進学したようです。
卒業記念全楽曲デモテープを作成し、皆の記念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とのことですが、3月卒業間近は企業研修や卒論や海外留学準備で叶わなかったとの事。
その後、全国に散り散りになったバンドメンバーが集まって演奏する事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んな長い話を書いたのは訳があります。
先日、このバンドメンバーと近しかった人から、メンバーのうち二人がもう亡くなったと言うことを聞いたからです。
このくだらない、おバカなバンドについて、どこかに残しておきたくて書きました。
ご冥福を祈ります。
5 notes
·
View notes
Text
無法複製的一道菜
■作者:楊秋生(美国)
2023-03-13 09:24
《文舞霓裳》文学专栏 第216期

【作者 楊秋生】祖籍河南,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教於大學。現居美國加州矽谷,為海外華文女作協創會會員,並曾任北加州作家協會會長,現任美國西北華文筆會顧問。出版有兒童書,小說《摺紙鶴的女孩》、《致女作家的十封信》、《生死戀》。小說曾改編為電視電影,並列於巡回文藝營書單目,《22號公車》曾獲得文苑文學獎小說組佳作獎。散文著有《心中有愛》、《相思也好》、《永不磨滅的愛》,曾獲海外華文著述獎及文學著述首獎,論文《試論融融「茉莉花酒吧」創作技巧與魅力》獲海外華文論文著述佳作,另譯有《神的名字》一書,列為各大學宗教系參考書目。興趣廣泛,並涉獵園藝、美食及國畫。
一直以為母親是不會做菜的。
出生官宦世家的外婆,嫁給外公的時候,帶著貼身丫鬟和廚娘作為陪嫁,母親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裡長大,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她不會做菜,似乎是極其自然的事。而母親嫁給父親後,父親事業如日中天,家裡有數人伺候著,哪裡需要母親洗手作羹湯?
父親倉促來台,分文未帶,家裡環境相當緊張,父親捨不得母親做家事,仍僱有阿婆幫忙洗衣燒飯,直到我出生之後,家用實在太緊,這才打住。照理當時父親長年駐紮金門,在沒有幫傭的情況下,家裡每件事情都是母親親手料理,包括六口的一日三餐。向來對幼兒時期發生的事情有著超強記憶的我,可以像一千零一夜每日一個故事如數家珍地講給大家聽,卻不知為什麼對於過往日常三餐吃些什麼,卻毫無印象。
五歲那年,家裡從台中搬到台南,父親堅持餐桌一定要買12人座的大圓桌,中間還要有個大轉盤。對擺在大圓桌上面的食物開始有印象,已經是兩年之後,父親從軍中退下來,親手掌廚開始。
父親對燒菜特別有天份,吃過的菜只要他喜歡,一定能夠複製出來。他為人海派又好客,家裡經常高朋滿座,每道菜都是他精心設計的獨家私房菜。他燒菜燒出名來,不知多少人上門送上禮,就只是為了能夠有機會來我家吃上一頓聞名遐邇的「將軍宴」。
母親因為身體一直不好,父親捨不得母親做家事,即使家裡請客,從買菜、洗菜、燒菜到洗碗,都是父親一手包辦,不讓母親插手。我懂事後,最多也只是在旁邊接手洗菜、切菜和洗碗等雜事。
記得有一天母親跟父親說,她這輩子都還沒有管過帳,能不能夠讓她管管看?
父親一口答應,說讓她管一個月試試看。
第二天早上大約十點半的時候,忽然聽到母親呼喚我們,說:「大家快來呀,看看我做了什麼好吃的東西給大家吃?」
我跑到餐廳一看,餐桌上擺了一個好大的不鏽鋼盆子,盆子裡頭裝滿了色澤非常漂亮的去殼蝦。
蒜香沙拉
「這是我做的,你們盡量吃。大家就當點心來吃,不算正餐喔。」母親臉上泛著溫柔笑嘻嘻地說。
我們五個孩子圍坐餐桌,連筷子都來不及拿,五隻手伸進盆子裡抓起蝦就吃。當時覺得那蝦真是好吃,全然沒有想到這個蝦母親是用什麼方法做的?調味鮮香,清爽美味,口感恰到好處,既不油也不膩,真是鮮美極了。在一個自稱菜龍,另一個自稱菜虎的兩位姊姊帶頭下,那一大盆比酒席上12人份的量還多上好幾倍的蝦,轉眼就被我們銷光了。啊,原來母親不但會做菜、手藝也極精妙,我從來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母親又端了一大盆子的醃黃瓜上桌。那醃黃瓜較之前一天的蝦,滋味毫不遜色,當然,又是被五隻手瞬間一掃而光。
第三天,換成一大盆酸筍,甭說那滋味有多迷人了,自然又是盆底朝天。
就這樣,一個禮拜之後,父親攤開帳本對母親說:「讓妳管家的結果,妳可是一個禮拜就把一個月的菜錢預算都花光了呢。」
西班牙海鮮飯
母親心服口服地把掌管大權交了回去,從此以後又回復到之前父親買菜掌廚的日常。
父親菜燒得好,又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錢燒出最值錢、最美味的菜來,我們經常吃得心滿意足,母親那個禮拜曇花一現的精妙手藝,很快地就淡出了我們的記憶了。
辦綠卡時因為懷孕不能照X光,移民局讓我生完孩子再補件。那天從醫院回來,母親興沖沖地對我們說:「中飯我煮好了。」,走到餐桌,只見盤裡一條蒸得漂漂亮亮的鹹魚,旁邊鑲著兩枚完美的荷包蒸蛋!先生一見大呼:「鹹魚蒸蛋——我最愛吃的。」

原來母親愛吃鹹魚。
我這才意識到我對母親了解得那麼少,她喜歡吃什麼似乎從來沒有人關心過。我想起母親管帳那個禮拜的鮮蝦、醃黃瓜和酸筍,似乎明白了裡頭盡是母親的愛好和鄉愁。
父母親移民到美國之後,照例還是父親掌廚。但母親愛吃魚,對於燒魚,父親似乎僅限於紅燒黃魚,自此燒魚成為母親的專利。每次去看望父母,母親多半希望我們留下來一起吃飯。母親的紅燒魚外香內嫩馥郁美味,舉箸大快朵頤之時,我似乎回到那個無憂年代,只顧著吃,從來沒想到要問母親如何燒出這麼美味的魚來。

被父親稱讚菜燒得不錯的我,幾十年來一直不停地自我挑戰,開創出許多私房菜,家裡也經常有朋友來訪,每每吃得賓主盡歡。母親尤愛吃我做的菜,有時吃得高興會說「我還要再添一碗飯」。我發現,我似乎走著和父親一樣的道路,寵著母親,做她喜歡吃的菜,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問過她:「你有什麼想吃的菜嗎?」也許,在她的心底,那盆鮮蝦是她的最愛。
近年來不知是不是年紀漸長的關係,情感變得更細緻敏感而脆弱,總不自覺地懷念起父母還健在的日子,一幕一幕的歡樂時光,總在我毫無防備的時候蹦出來,清清如水的記憶之河,一輪明月在連漣漪中震盪著,星子們一眨一眨的,彷彿也在哭泣。在沉靜的夜晚,闃靜無聲的清晨,母親恬靜如幽蘭隱���散發著幽香,素淡如秋日菊花,淺淺笑著呼喚我們吃飯的身影,總會在腦海裡縈繞不去。

香蔥肉鬆卷
經過歲月的沈澱,那一盆鮮香利爽的鮮蝦,在腦海裡益發甜美,使得我費盡心思想要複製。然而我這雙被文友稱為像魔棒的巧手,始終複製不出來記憶中的滋味,母親的鮮蝦遂成為絕響。
窗外屋簷滴落的雨珠滑過窗戶,彷彿一串串眼淚,母親喚著我們吃蝦的面容清晰如昨,我的眼角濕了。我已分不清是懷念母親那道菜,還是母親寵著我們的心?抑或是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四喜丸子
0 notes
Text
读书笔记 |《单词的历史:英语词源漫谈》趣词摘录
这是一本讲英语词源的书,书名的原文叫做《Midwives, marathons and mumbo jumbo: a dictionary of word and phrase origins》,点得很清楚,是一本关于「单词和习语起源的词典」,中文翻译成「单词的历史」反而让人误以为是个系统讲词源学的大部头。
作者: 马丁·H·曼瑟;译者: 崔峰;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 2015-5
其实本书只有240也,体例如词典,一个词一段解释,很快就能读完。不过从整体内容来说,有点枯燥无味,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免不了要从中摘录一些相对有趣的词条。

下面就夹叙夹议着列一列。
abracadabra (表演魔术、施魔法时所念的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
魔术师表演魔术时会使用abracadabra这个咒语。该咒语可溯源至希腊咒语abrasadabra。诺斯替教派、巴希理德学派、的教徒们在祈求神助时使用这一咒语。它也可能来源于abrasax,其最初是由希腊字母组成的咒语或护身符,人们相信它是有魔力的;从公元2世纪起,abrasax又被认为具有神性,且受到诺斯替教派的崇拜。这一咒语中包含了数字365,代表365重天,也表示重天中的精灵,它们是神的365个发散体。
另一种解释认为该词来源于三个希伯来词语:即Ab(圣父)、Ben(圣子)及Acadsch(圣灵)。
如果你念得够快,这个词就会变成:Wubba lubba dub dub!

aftermath 后果,创伤
该词指不幸或灾难(如战争、洪水等)发生后随即产生的余波、后果。该词的意思由 after和math的字面意思延伸而来。math 表示一拨收割后的草,因此 aftermath 表示同一季节内再度收割的草。
如果创伤是被再次收割的草,那我们的悲伤就如afteralliumtuberosumcutting

agnostic 不可知论者
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某个词是在何时由何人创造的,但agnostic是个特例。186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倡导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创造了该词。当时他是形而上学学会(the Metaphysical Society)的一员。赫胥黎认为,人们无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所以他想创造一个单词以表示某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有物质对象才是可知的,所以把 a(希腊语中表示“不”的意思)与 gignōskein(希腊语中表示“知道”的意思)结合起来,创造了agnostic。赫胥黎原本用该词指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某个人,但在现代英语中它的意思略有变化,指怀疑上帝存在的人,或者更笼统地指对特定事物持怀疑态度的人。
基本上所有西方主流语言都是直接引用这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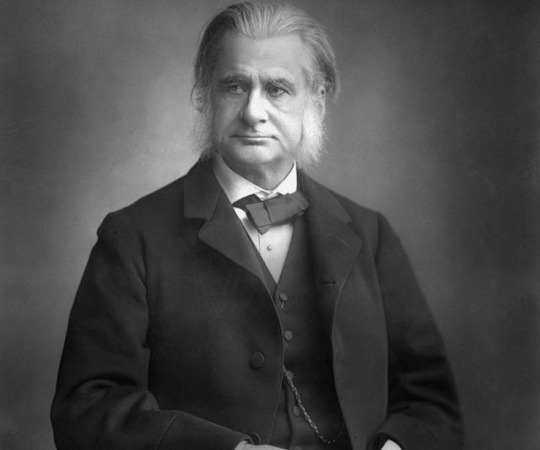
antimacassar 椅背套
19世纪,润发香油被引进英国,其中含有大量望加锡油。据说此油的原料产自望加锡(Makassar,即现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乌戎潘当〔Ujung Padang〕)。该发油颇受欢迎,使得望加锡成为商标名。由于沙发椅沾上发油后易留下污渍,所以人们就发明了antimacassar(由 anti和macassar 组成)。antimacassar是一种装饰性布料,可以套在椅背上作吸油之用,从而保持椅子清洁。现今,一些住家、火车车厢和飞机内仍在使用antimacassar的纸制椅罩。
又是一个地名变名词的案例,还加上一层反转,还是德语里的Sofaschoner更简单易懂些。

atlas 地图册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是泰坦神族(Titans)的巨神之一。因为他企图推翻宙斯的统治,所以被罚以双肩扛天度其余生。地图绘制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ror,1512—1594)曾采用阿特拉斯擎天图作为一本地图册的扉页插图,该地图册于16世纪末出版。后来atlas就被用来指称地图册。
在建筑物中,atlas(复数形式是atlantes)指的是男像柱,它们被用作上横梁的支撑柱。而caryatids(复数形式是caryatides)指的是女像柱,源自希腊语Karyatides,指的是希腊城邦卡黎亚(Caryae)的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的诸位女祭司。
Atlas → Atlantes,特别的复数形式,不过atlases好像也是存在的。

atone 补偿
该词表示为所做的错事感到愧疚,并补偿过失。它源自 16世纪产生的一个名词 atonement,用以表达"at one"的状态(at-one-ment)——即与上帝保持一致。后来这种“协调”之意转而表示对错事进行弥补。
德语里表达类似含义的是一个长词:Wiedergutmachung,有修复的意思。

batty 疯疯癫癫的
batty 形容某人言行古怪或有点疯疯癫癫。该词可能源自短语have bats in one's belfry。人们认为安布罗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在 20世纪初第一次使用了这一短语,指的是钟楼里的蝙蝠。每当钟敲响时,蝙蝠便会疯狂地乱飞,就好像一个疯子心神不安、胡思乱想一般。
类似的词还有batshit(极不合理的),可能源自apeshit(像猿猴一样因为愤怒或兴奋失去控制),以及squirrelly(可能源自松鼠般的不稳定)

beggar 乞丐
该词可能源自 12世纪比利时神父兰伯特·伯格(Lambert Le Bègue)的昵称,即“结巴兰伯特”(Lambert the Stammerer)。他在列日(Liège,今比利时东部城市)创建了一个女修道会,修女们被称作Beguines。她们过着简朴的、半世俗的集体生活。会员无须立誓,并可拥有私人财产,还可随意返俗。后来又出现了类似性质的兄弟修道会,成员被称作Beghards。他们拥有共同财产,但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所以他们中有不少人靠救济金为生,无自尊可言。故而,Beghards 一词保留了下来,并变成了beggars。
所以说,beggar并不是源自beg,而是从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代称。

blurb (印在书籍等护封上的)推荐广告
该词指简短的广告,尤指出现在书籍封面上的广告。它系美国幽默作家、插图画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1866—1951)为推介他的新书《你是庸俗之人吗?》(Are You a Bromide?)而创造的。
20世纪初,美国小说的封面上通常会印一张美女照吸引读者。伯吉斯对此进行了恶搞,把一幅他称为"Belinda Blurb 小姐”的美女照印到了护封上,画中的小姐一副病殃殃、无精打采的样子。他这样做是为了希望“以她的封面为护封广告,以期终止此类广告”(blurbing a blurb to end all 封面为护封广告,以期终止此类广告”(blurbing a blurb to end all blurbs)。自此以后,人们便常将 blurb 一词同书籍封面上的广告联系起来。
看来腰封宣传真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情。

boycott 联合抵制
boycott a person,organization,etc.指拒绝与某人、某机构等有业务关系。该短语除了具有“不同意”的含义外,也常指试图强迫他人、机构等接受特定条件的某种手段。boycott 一词出自查尔斯·肯宁汉·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1832—1897)上校,他是一名土地承租管理人。
杯葛在退役后,受雇于厄恩伯爵(the Earl of Erne),管理爱尔兰梅奥郡(County Mayo)的地产。1880年,爱尔兰土地同盟(the Irish Land League)试图进行土地改革,倡议地主削减佃农地租,并声称凡拒不执行此倡议的地主应遭驱逐。结果杯葛因为拒绝减租而立即遭到驱逐。他的工人被迫离开他,商人拒绝给他供货,他的妻子也受到了威胁——他不得不携妻子仓皇逃往英格兰,以躲避迫害。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联合抵制”的事件就这样大获成功。
主要的西方语言基本都沿用了boycott,只不过在拼写上各有调整(并加上了动词词尾),如法语boycotter、德语boykottieren、意大利语boicottare、西班牙语boicotear、世界语bojkoti…可怜的杯葛上校。

browse 浏览
该词指随意浏览书刊杂志等。它源自古法语brost,原义指鹿、羊等动物食用的嫩苗、嫩叶和嫩枝。所以该词既保留了“吃叶”这一本意,又具有了“悠闲地择取事物”这样的比喻义,如浏览杂志中的段落,或慢悠悠地逛商店,试图找到有趣之物。
「悠闲地择取事物,试图找到有趣之物」,这个意象真是太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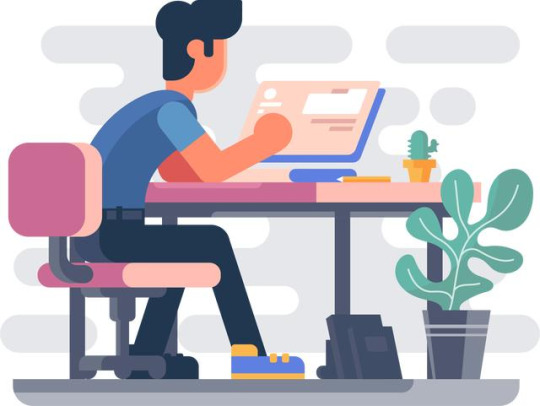
burgle 入室行窃
someone burgles a house指某人入室行窃。动词 burgle 源自名词 burglar,也就是说,burgle是个逆成词——即去掉已知单词的后缀以形成另一相关词语。比如,人们以为以 -ar,-er,或 -or 结尾的名词是由已知动词加上"doer"之类的词尾构成的,这就使 pedlar和editor 被误解为是由 peddle和edit 分别加上相关词尾衍变而成。
其他逆成词还包括 commute(commuter的逆成词)、diagnose(diagnosis的逆成词)和televise(television的逆成词)。
关于删出来的逆成词,还有哪些,可以参考这个列表: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back-formations

Busman's holiday 有名无实的假期
该短语指照常工作的节假日。据说在 20世纪初,伦敦很多公共马车的司机非常喜爱他们的马匹,为了确保顶替轮班的司机对马儿好一点,他们在休息日作为乘客,坐上自己的车子,以确保马儿被照管妥当。
对当代新媒体、广告等行业从业者同样适用,Mad Man's Holiday.

chortle 咯咯地欢笑
chortle指满意地笑或被逗得直笑。这是英国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在他的童话《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2)中造的一个词,由 chuckle(抿着嘴暗笑)和snort(哈哈大笑)缩合而成。squawk 一词也是由卡罗尔所造,现在亦广为使用,它是由 squeal(尖叫)和squall(哇哇叫)综合而成。既然把两种意思“压缩”成一个单词,卡罗尔便把这样的单词叫做 portmanteau words,portmanteau在当时是一款时尚的旅行箱。
造词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类似的还有slithy(lithe+slimy),现在「混成词」就叫做portmanteau,不过目前逐渐被blend取代了。

earwig 蠼螋
该词指蠼螋,它是一种小昆虫,身体尾部长着一对螯。该昆虫得名自古英语ēarwicga:ēare指耳朵,wicga 则指昆虫或甲虫。根据过去流传的迷信说法,这种昆虫会爬进梦中人的耳朵,然后又钻进人的大脑,故得此名。作为该词一要素的wig可能也与 wiggle(扭动,蠕动)有关。在其他语言中,这种昆虫也有类似的名词:如法语的perce-oreille,字面意思为“刺穿耳朵者”;德语的Ohrwurm,字面意思为“耳虫”。
「蠼螋」的读音是:chyu sou,两个典型的形声字。

eavesdropper 偷听者
该词指窃听者。eaves指屋檐,在阴沟和排水管还未发明之前,屋檐能够使雨水滴到屋子之外。雨水所滴之处曾被称为eavesdrip,后衍变为eavesdrop。而檐下滴水之处靠近窗户,正是偷听屋内人说话的理想场所。
太形象了。

electricity 电
古希腊人已经了解了电这一能源形式。他们发现,通过摩擦琥珀可产生静电,吸引稻草和其他很轻的物质。该词源自英国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根据希腊语ēlektron(琥珀)所创的electricity 一词。吉尔伯特以其在磁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他的论文《磁论》(De Magnete,1600)而闻名于世,被称作“电力之父”。吉尔伯特也将 electric force(电力)、magnetic pole (磁极)等术语引入英语。
在奉行纯化政策西方语言里,对「electricity」这个词总要进行一番再创造。比如冰岛语里的rafmagn = raf(琥珀)+ magn(力量),等于把希腊语词根直译了一遍;匈牙利语的villamosság源自villám(闪电);最有意思的是芬兰语的sähkö,1845年由物理学家Samuel Roos创造,源自动词sähähtää(短暂发出嘶嘶声)和säkenöidä(冒火花)的合成。

intelligentsia 知识阶层
该词指社会中对文化艺术、政治等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根溯源,它源自拉丁语intelligentia(感知力或理解力)。令人好奇的是,intelligentia是从俄语中借用而来的。它在俄语里指“俄国革命”前社会上的那些“有志于知识性活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第2版)的一群人。20世纪的前25年,该词进入英语中。
俄语的原文是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intelligéncij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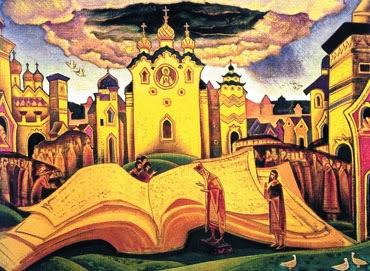
laser 激光
激光能产生高强度光或其他形式的电磁辐射,在切割硬物、全息图、电信、手术等方面用途广泛。laser是一例首字母缩略词:起初它名为light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器),各单词首字母组成 laser。由于全称表述累赘而形成缩略词的其他科学术语还包括:AIDS(艾滋病),源自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radar(雷达),源自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及sonar(声纳),源自 sound navigation ranging(声音导航与测距)。
一般能组成音节的缩写词能容易独立成词,比如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不过USA就没人念成u-sa;此外音节也可以组合,例如Gestapo(Geheime Staatspolizei),翻译也很妙:盖世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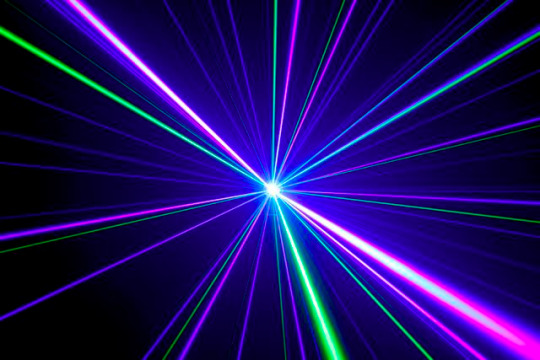
loo 厕所;盥洗室
loo 为口头语,尤指英式英语中的厕所。在几种词源解释中,最有可能的有两种。其一,一个英国人试图发法语le lieu(地点)的音,have time off in lieu 中的lieu 常发音为loo。其二,它是Gardy loo的缩写形式。在还没有下水道的年代里,家庭主妇们把夜壶倾倒至窗外的街道上时会发出“Gardy loo!”的警告。Gardy loo 在法语中写作gardez l'eau(小心有水)。

loo = l’eau,没毛病。
mesmerize 迷惑,迷住
someone is mesmerized by something指某人为某物神魂颠倒,仿佛受了魔咒或被催眠了一般。mesmerize 出自奥地利医生、催眠师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之名,他是首位将催眠术运用于医疗的人。梅斯梅尔出生于奥地利,后来在维也纳行医。他认为自己行医之所以成功,源于他使用磁铁作为催眠工具。
尽管那些被他治愈的病人给予他莫大的支持,他还是被奥地利当局从维也纳驱逐出去,于1778年移居巴黎。在那里,他的治疗技术变成了时尚。
1784年,路易十六任命了一个科学委员会调查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梅斯梅尔是个吹牛皮的骗子。他不得不逃离巴黎,在瑞士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他相信他的成功是由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而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催眠技术。
又一个人名进入词典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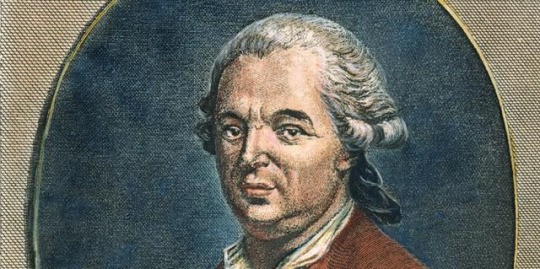
moron 蠢人,笨蛋
该词现主要是表达某人很蠢的一种粗俗的方式,它原本有精准的科学意义。1910年,在美国低能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Feeble-Minded)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博士(Henry H.Goddard,1866—1957)建议用此词指心理年龄在 8和12 岁之间、智商在 50和70 之间的精神不健全人士。该词源于希腊语mōros(愚蠢)。
这个词现在不够政治正确,某些情况下除外。

news 新闻;消息
该词指广泛传播的有趣或者值得关注的事件。常有人以为这个单词来源于指南针的四个方向:北(N)、东(E)、西(W)、南(S),因为新闻常常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其实该词的来源并不复杂:中古英语中该词的拼写是newes,模仿的是古法语noveles 或中世纪拉丁语nova,意为“新事物”。人们之所以认为该词的来源与指南针有关,估计是因为有些报纸习惯在报头放上地球的图案,并在上面加上指南针的四个指向。
「这个单词来源于指南针的四个方向:北(N)、东(E)、西(W)、南(S),因为新闻常常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有趣了。

nice 好的;美好的
恐怕没有哪个词的词义像 nice 这样变化如此之大。现代英语中该词表达赞同之意,有“好”、“美好”的意思。该词源自拉丁语nescius(无知的),13世纪传入英语,表示“愚蠢的”。其意思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14世纪时,它为“放荡”、“好色”之意;到了15世纪,则形容“害羞的”;16世纪时,它又指“吹毛求疵”或“细微差异”:a nice distinction(精细入微的区别)和a nice point(敏锐地指出)等现代词组中仍保留了这层含义。直到 18世纪,该词才具有了现代意义。
Nice的意味今天依然很微妙,有点像微信里的微笑表情。

OK
该词用以表达肯定的态度。对其来源,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主要的观点。有人认为该词代表oll korrect,是all correct的滑稽拼法,造于1938年。另有人认为Old Kinderhook的首字母缩写才是OK的来源,Old Kinderhook 即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1862)的出生地,后来也成了他的外号。马丁曾于1840年参加总统连任竞选,OK 俱乐部就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而成立的。他后来落选,所以当然不 OK 了。
不管该词起源为何,它和它的变体 okay 已经深深根植于英语和其他语言中。正如斯图尔特·弗莱克斯纳(Stuart Flexner)在其著作《我听见美国在说话》(I Hear America Talking)中所言:“OK是最流行的典型美语。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在美国,它每天的使用频率高达上百万次。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不但自己用OK,也凭此判断那些说 OK的就是美国人。”
OK才是真正的世界语,连世界语里都有个词叫okej。

onomatopoeia 拟声词
该词指象声词,是模仿它所代表的事物或行动的词。如buzz(嗡嗡声)、crash(碰撞声)、hiss(嘶嘶声)、moo(哞)、sizzle (嘶嘶声)。模仿描写对象声音的诗歌也是象声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钟声》(The Bells):
Keeping time,time,time,
In a sort of Runic rhyme,
To the tintinnabulation that so musically wells
From the bells,bells,bells,bells.
合着一种北方神秘的旋律,
合着那悠扬快活的丁丁锳锳,
铃声流出那小钟般的银铃,
丁锳,丁锳,丁锳。
该词源自希腊语onoma 一词,由 onoma(名称)和poiein(制作)组合而成。
拟声词这个话题,本身就够写无数篇论文了。这里只说说几个新造的拟声词,比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造的:tattarrattat,用来形容敲门的声音;60年代的《蝙蝠侠》电视剧,在战斗场景里,屏幕上会出现漫画风格的拟声词:wham!, pow!, biff!, crunch!, zounds!;漫画作家Don Martin经常自创拟声词,比如thwizzit,是表现「从打字机中拉出一张纸的声音」,粉丝们甚至还为此编了个字典,记录这些拟声词的含义。

palindrome 回文
该词表示“回文”,即顺读和倒读都一样的单词、短语或句子。它源于希腊语palindromos(再次跑了回来),其中 palin 表示“反过来再来一次”,dramein 表示“跑”。最早的回文是由古希腊人设计出来的。英语回文词的例子有 Hannah(人名:汉娜)、level(水平)、minim(微量水平)等。英语中最长的回文词是redivider(重新划分)。拿破仑曾说过: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在见到厄尔巴岛之前,我本无所不能。”
还有 19世纪的一组对句:
Dog as a devil deified.
Deified lived as a god.
魔鬼一般的狗被奉若神明,被奉若神明的它如神一般生活。
最长的回文故事有 66 666个单词,由爱德华·毕尔布(Edward Berbow)所作。它的开头是Al,sign it,“Lover!”,结尾是revolting,Isla.
这个回文故事似乎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查到类似的文本,另外这个作者似乎应该是叫Benbow而非文中的Berbow。
前面提到乔伊斯创造的拟声词tattarrattat,被《牛津英语词典》认定是英语中最长的回文词。《吉尼斯纪录大全》则认为是detartrated,一个化学术语的过去分词,意为「去除了酒石酸盐的」。
另外吉尼斯纪录还认定,芬兰语中的saippuakivikauppias(皂石供应商)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长回文词。
除此之外,英语中还有两本「回文小说」,David Stephens于1980年写的《Satire: Veritas》,一共58795个字母;Lawrence Levine于1986年写的《Dr Awkward & Olson in Oslo》,一共31954个字母。此外,Demetri Martin还写过一首224个词的回文长诗:Dammit I'm Mad。

pandemonium 喧闹,大混乱
该词指喧哗吵闹的状态。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1667)第1册中创造了该词。弥尔顿用此词作为地狱首府的名称,而所有的邪灵都来到首府参加会议:
"A solemn Council forthwith to be held At Pandæmonium,the high Capital of Satan and his Peers."
“万魔窟是撒旦和其从众的首府,在那里将立即召开一次庄严的会议。”
该词源于希腊语pan-(全部)和daimōn(精灵)。
这个词本身就非常有庄严感。

posh 漂亮的,时髦的;高档的
有关它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颇具诗情画意,认为该词源自英国人乘船定期往返于印度的时代,当时的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为了避免强烈阳光的照射,一些乘客在往返时都要住在船的遮阴侧,即去时住在船的左舷边(port out),回来时住在船的右舷边(starboard home)。取这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即为posh,指有地位、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付得起这样的舱位价格。虽然这种说法颇为流行,但缺少证据。第二种说法虽然不那么精彩,,认为该词源自过时的俚语单词 posh(花花公子或钱),最早可能出于吉卜赛人之口。
果然还是第一个说法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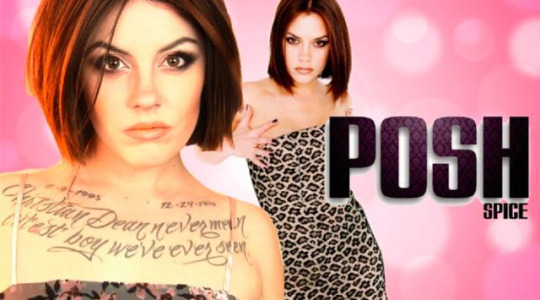
robot 机器人
该词指代替人类执行任务的自动机器,它出自捷克语robota(工作或奴役)。1920年,捷克剧作家、小说家卡尔·恰彼克(Karel Čapek,1890—1938)创作了戏剧《罗萨姆万能机器人公司》(Rossum's UniversalRobots),其英文版本于1923年在伦敦公演,剧名中的robot 遂进入英语中。剧中的人造机器人虽然没有生命,但却能熟练地操作机器。
形容词 robotic(机器人的或像机器人的)由美国科学家、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于1941年创造出来。
像中文中「机器人」这种翻译,在世界范围内很少见,不过冰岛语总能给你惊喜,vélmenni(机器人) = vél(机器)+ menni(合成词中表示「人」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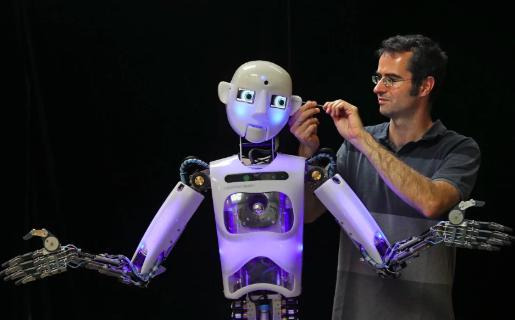
serendipity 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本领
该词指意外发现有趣事物的本领。175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尔浦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创作了波斯神话故事《锡兰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从而创造了serendipity 一词。故事中的英雄们拥有如此才能:
"they were always making discoveries,by accidents and sagacity,of things which they were not in quest of."
“他们总能凭着运气和睿智,发现他们并没有寻求的东西。”
「意外发现有趣事物的本领」多么迷人的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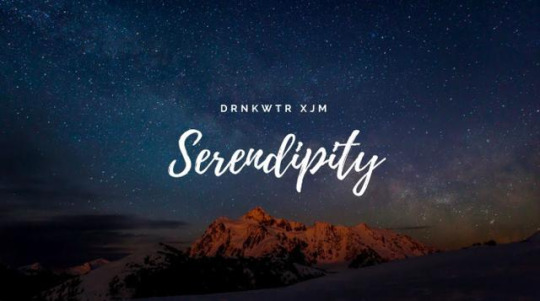
smog 烟雾
smog(烟雾)是由 smoke(烟)和fog(雾)组成的混合词。1905年,在公共健康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H.A.德佛(H.A.des Voeux)博士创造了该词,用来形容伦敦烟雾弥漫。其他混合词还包括:binary(二进制数)和digit(位数)组成的混合词 bit(二进制位),breakfast(早餐)和lunch(午餐)组成的混合词 brunch(早午餐),camera(照相机)和recorder(录音机)组成的混合词 camcorder(摄像机),motor(汽车)和hotel(旅馆)组成的混合词 motel(汽车旅馆),以及transfer(转移)和resistor(电阻器)组成的混合词 transistor(晶体管)。
最近很火的Brexit、Megxit也是如此。其实和制英语中其实也有很多混成词,比如パソコン,就是パー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 personal computer )的混成,ポケモン( Pokémon)是ポケット・モンスター(pocket monster)的混成。

ventriloquism 腹语术,口技
该词指腹语,它是一种发声艺术,使声音听起来并非出自说话者的口腔。口技演员常手持一只玩偶,通过操纵玩偶使其张开嘴巴和移动躯干。该词的词源是ventriloquism,由拉丁语单词 venter(腹部)和loqui(说话)组成。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既然声音不是从口技人的嘴里发出的,那么一定是出自于其腹部。
一直没有搞懂腹语术是怎么练成的。

vitamin 维生素
该词指维生素,它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是保持身体健康和成长的重要物质。1912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Casimir Funk,1884—1967)创造了该词。起初,冯克把它拼作 vitamine,由两个拉丁单词 vita(生命)和amine(氨)组成,当时人们以为维生素中包含了氨基酸。但后来人们发现,维生素中并没有氨基酸,遂去掉了vitamine 中的e。
还是喜欢另一个翻译「维他命」,当真是形神兼备。

以上。
3 notes
·
View notes
Text
这太搞笑了孩子们,不论长得多崎岖的立体男,做成棉花娃以后都会变成这种千人一面的婴儿肥大眼萌。老男人们也是无痛减龄了
3 notes
·
View notes